內容連載
12 拓展人類生態位 Expanding the Human Niche
羅馬人在各種氣候條件下都會打仗,憑藉著出色的紀律,他們盡可能保持健康與活力。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人類是唯一能夠在從赤道到極地的所有國家生活和繁衍的動物。就這項特權而言,似乎只有豬能與人類相提並論。
——愛德華‧吉朋,《羅馬帝國衰亡史》
蜿蜒小路穿過玻利維亞的亞馬遜河流域,交織成路網。有些道路高於周圍地景,好像河堤道路一樣;少數道路之間還有間隙。對外行人來說,這個路網似乎是隨機形成的,是自然力量的產物。然而事實卻令人咋舌。這裡的道路與河堤路網,完全是由玻利維亞的旱地漁民以手工興建的。河水會不時地淹沒整個地區,而在洪水退去後,水就留在堤道阻隔的水坑與池塘中,道路縫隙中布滿了漁網和陷阱,誘捕試圖想要跟著退潮返回河裡的魚。等到洪水完全退去,這些水塘就形成了綠洲,富含可食用的植物,為旱地漁民補充飲食所需。
一般人看慣了歐洲或北美那種整齊一致的田野,或是光禿禿山坡上散落著羊群的地景,會認為這似乎是一種不尋常的耕作方式。我們總是用先入為主的觀念來看任何新的地景:對西方農民來說,亞馬遜是一片未馴服的叢林,然而事實上,亞馬遜地區的人口密度曾經比現在大得多,他們居住在廣闊的花園城市裡,擁有豐富的都會與宗教建築,還在肥沃的土地上耕作。熱帶美洲有許多其他地區也是同樣的情況。十五世紀末,在「征服者」抵達這裡之前,他們的疾病似乎就已經先到了,所以當西方人的目光首次關注亞馬遜時,叢林中的古代文明已幾乎完全消失,只留下一片密林。因此,我們所認定的亞馬遜原始荒野絕非如此——而是可以追溯到一萬兩千多年前人類活動的產物,甚至追溯到智人首次來到這個地區的時候。
人類活動改變地景
這樣的認知強迫人類用全新的眼光來看待自己的環境。整齊的田野和光禿禿山坡上散落著羊群的地景其實也是人造的,完全是人工創造出來的場景,從某個層面來說,也像商業街和煙囪一樣具有工業化特徵。激進的活動人士以破壞鄉村美景為由,反對風能或太陽能發電等新開發項目,但是他們常常忘了:我們深愛的鄉村其實遠非自然。我們的鄉村完全是人造的,只有透過不間斷的警戒才能維持下去。如果任自然發展,樹木會重新占據這片土地。一萬年前,歐洲和北美東部大部分地區都覆蓋著森林。如今,隨著農業衰退,世界上的這些地方又重新披上森林的外衣。在北美東部的早期殖民地是一片田野和農場的混合體,然而隨著拓荒者的腳步向西部蔓延,原本的田野和農場很多都荒廢了,又重新變回森林。如今,英國的森林覆蓋面積達三萬兩千平方公里——約占國土面積的百分之十三——這幾乎是一九〇五年的三倍。在人類了解到英國人異常喜愛樹木之前,全世界的情況都是一樣的。一九八二年至二〇一六年間,全球樹木覆蓋面積增加了兩百二十四萬平方公里,約莫是英國陸地面積的九倍。熱帶地區的森林砍伐占據了各大媒體的頭條,但是溫帶地區重新造林的面積也不遑多讓。大部分變化可以歸結為一個因素——人類活動。
向來都是如此。地景從來都不是靜止不動的,自從智人遍布世界各地以來,可能已經不再有任何地景可以視為完全原始的。人類活動甚至延伸到世界上人類很少或從未涉足的地區,甚至連太平洋上最偏遠的無人島海岸線上,也妝點著(如果可以這麼說的話)許多人類的垃圾。
每個物種都會建構自己的生態位
動植物會改變它們生存的環境,只是因為它們在那裡生存。從生態學的角度來看,每個物種都會創造或建構自己的生態位,這些生態位可能很小,也可能很大。舉個小例子:榕果小蜂(fig wasp)一生大部分的時間都生活在牠們從無花果樹慢慢建構出來的特殊結構中,這些結構就是我們認為的無花果,也就是樹的果實。因此可以說,這些昆蟲建構了自己的生態位,是原本並不存在的東西。
另一個極端的例子出現在上一個冰河時期,當時歐亞大陸的大部分地區都籠罩在一種名為「猛瑪象草原」(mammoth steppe)的生態系統之中。這種環境支持了豐富多樣的植物——大部分是草類和草本植物——這在任何現代生態系統中找不到。在茂盛草原上吃草的,是大量幾乎難以想像的大型動物,而不只是猛瑪象——我在第五章已經討論過這個主題。冰河時期末期的氣候變遷導致猛瑪象草原枯萎,依賴草原生存的動物也隨之滅亡(儘管人類無疑加速了這個過程)。動物和植物互相依賴——植物從動物的糞便中汲取營養,而動物則獲得豐富的飼料。每種生物都從其他生物那裡開闢出自己的生態位。
人類是自然的一部分,也創造了自己的生態位,但是人類將生態位結構提升到了另一個層次。關於人類建構生態位,有一點最令人驚訝,那就是我們在歷史大部分時間裡一直都在做這件事——或許比那些看到亞馬遜和完美雨林的人所意識到的還要更長久。數千年,乃至於數百萬年來,人類活動一直在改變環境。人類的祖先直立人是我們所知的第一個能夠馴服和使用火的生物。例如,有跡象顯示早期人類用火來清理森林,無論是為了驅趕林中獵物以便進行狩獵,或是為了引誘獵物到長了新鮮植物的森林空地,或是為了促進對他們有用的植物生長。巨型動物——也就是體型比大型犬要大的大部分動物——在上一個冰河時期末期消失,主要也是歸因於人類的活動。這對整個生態系統產生深遠的影響,影響及於一切,從火的延續到水果和種子的傳播等等,甚至還影響了氣候。例如,由於過度捕獵導致大型草食動物消失,進而促進了森林的生長,而森林比裸露的地面更能吸收太陽能。即使在史前時期,人類的活動也共同改變了氣候。
人類的干擾與生物多樣性
農業發明強化了人類生態位的影響。砍伐森林和耕作會釋放二氧化碳,而種植水稻則導致向大氣中排放的甲烷增加。甲烷是一種比二氧化碳更厲害的溫室氣體。但是農業最大的影響——或許超過其他——就是將動植物遷移到世界各地,或許遠離它們的原生地。這裡說的還不只是家畜,還有害蟲和病原體。我們已經習慣了這種遷徙,甚至認為在某個地方出現的陌生動植物一定是一直生長在那裡的。像是在英國鄉間很常見的兔子,其實是跟許多其他動植物一起由羅馬人引進來的。有一次,我在夏威夷一家飯店的陽台上吃早餐,環顧花園,發現我所看到的每一種植物和鳥類都是引進的:夏威夷的本土動植物要不是已經滅絕,就是只局限在幾個相對偏遠的叢林地區。回到比較接近我們的時代,如果沒有辣椒,印度菜或中國菜會是什麼樣子?如果沒有馬鈴薯,愛爾蘭曲折的歷史又會是什麼樣子?這兩種植物都原產於美洲,並在過去五百年內才被帶到新的家園。整個動植物群的遷移最終讓地景更適合人類居住,因此拓展了人類的生態位。
這就是考古學家妮可‧波伊文(Nicole Boivin)及其同僚所謂的「移植地景」(transported landscapes),尤其是島嶼受到影響最深。例如,在人類抵達塞浦路斯島之前,那裡幾乎沒有可供人類生存的東西,早期在此登陸的農民帶來了生存所需的全套物品,不只是所有農作物和家畜,還有野生動物,如鹿、野豬和狐狸。類似的故事在全球各地的島嶼上都曾經發生過,如果沒有殖民者帶來的動物和植物,這些島嶼根本無法養活人類。
人類的影響,以及人類將新物種引入它們以前從未生存過的地方,對當地的生物多樣性造成了極大的破壞。生物多樣性喪失,如森林砍伐,占據了各大媒體的頭條。因此,當你發現人類的干擾實際上可能增加了生物多樣性的時候,可能會大吃一驚。
生態學中有一個原則叫做「中度干擾假設」。當生態系統完全不受外力干擾,可以自然發展時,可能形成只有一種——或是少數幾種——物種占據主導地位,進而降低生物多樣性。在另一個極端,當生態系統受到某種巨大災難的破壞——無論是自然災害(如火山爆發、小行星撞擊)或人類活動造成的災難(例如建造了天堂或是設置停車場),生物多樣性也會減少。然而,當干擾程度處於兩個極端之間的某個中間位置時,生物多樣性就會蓬勃發展。想像一下,當森林裡一棵老樹倒下並死去時會發生什麼事。樹木倒下後產生一塊陽光充足的空間,這裡很快就被大量無法在連續森林覆蓋下生存的植物和動物占據;老樹的殘骸腐爛,為大量昆蟲、真菌和其他生物提供了家園。智人改變地貌,也創造了原本不可能形成的各種棲地,並迫使原本不會接觸到對方的不同物種進行接觸,其最終結果就是增加了生物多樣性,從某種程度上來說,確實是如此。
早在有歷史記載之前,人類就一直在改變現狀,為了無所不在的自己創造生態位。正如波伊文及同僚所說的,「『原始』地景根本就不存在,而且在大多數情況下,幾千年來都不曾存在過。大多數地景都是由數千年來人類活動反覆形塑的。」人類的生態位建構始終都是「地球的主要演化力量」——過去如此,未來也還是一樣。
人類應對變化:遷徙、適應、擴大生態位
所有這些人為造成的破壞,都發生在過去約六千年、氣候相對穩定的背景下——涵蓋有歷史記載的整個時期。智人已經習慣了這種穩定。或許過得有點太舒服了。
在此期間,人類似乎已經習慣了這種比一般認為要更狹窄的生態位。一般而言,人們傾向於居住在年平均氣溫在攝氏十一至十五度之間的地方,不過印度季風地區是個例外,那裡的人們集中在年平均氣溫約攝氏二十至二十五度之間的地方。目前對氣候變遷的預測顯示,未來五十年內氣溫生態位的變化,可能比過去六千年內的變化還要更大。三分之一的人口將經歷年平均氣溫超過攝氏二十九度的天氣——目前這種情況只出現在不足百分之一的地球表面,大部分都在撒哈拉沙漠。面對這樣的變化,人類的反應不外乎遷徙、適應,或二者兼具。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當前這個氣候穩定的時期其實非比尋常。在整個智人的歷史中,氣候變化的速度都在轉瞬之間,有時是長時間的極度寒冷,其間穿插較短的溫暖時期,有時甚至連高緯度地區也會出現熱帶的溫暖氣候。人類透過遷徙和適應,尤其是透過擴大人類的生態位,從容地應對這些變化。
當一位我們南方古猿的祖先首次將兩塊岩石撞擊在一起,發現碎片的鋒利邊緣可以用作挖掘、切割和切片的工具時,人類的生態位就開始擴大了。甚至在烹飪出現之前,古人類就發現可以用石頭搗碎植物的纖維物質,或用石頭砸碎動物骨頭汲取營養豐富的骨髓,拓展了他們的視野——不論在營養上、概念上或技術上。火的發明改變了整個模式。人類不僅可以開始烹煮食物——釋放更多營養素並殺死寄生蟲——他們還可以用火來硬化石頭邊緣,利用熱來進行化學實驗(尼安德塔人可能用火從樺木中製造出有用的焦油狀粘合劑),還有最重要的是,改變他們所居住的地景。例如,早在農業發明之前,人們就用火焚燒大片土地,驅趕獵物。
人類最初只是機會主義者,在熱帶大草原上拾荒和掠食,但是藉助火、人造居所和衣物,將生態位擴充至較冷的地區。順便一提,服裝的發明為寄生蟲創造了一個全新的生態位——如前文所述,人體蝨子完全依賴人類的衣服,並且是在人類發明服裝時從頭蝨演化而來的。人類適應了在所有環境中生活,從看似貧瘠的北極到熱帶雨林的複雜生態系統,對於他們在大草原的祖先來說,這兩種環境都是無法涉足的禁區——而以地質時間來說,這一切都發生轉瞬之間。儘管過去六千年的氣候相對穩定,但是人類利用這段時間創造了完全人造的全新棲地。這些我們稱之為「城市」的棲地逐漸有了自己的氣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由棲地的居民來控制,成了目前大多數人類生活的棲地。可是人類的影響卻無所不在。從城市到雨林,從海岸到高山,人類的生態位現在已經遍及整個地球。
好啦,現在我來談談過去幾章的重點。人類有機會可以避免滅絕,就是進一步擴大自己的生態位。他們可以透過移居太空來實現這一點,不過速度必須要快——發射窗口很窄,而且正在逐漸關閉。未來一、兩個世紀的人口急劇下降將對實現此一目標所需的技術創新造成嚴重壓力——其中包含多種多樣的技術,像是學習創造真正封閉且自給自足的生態系統、讓太空棲地適宜人居所需的人工光合作用,以及移動大型天體的力學原理。這些必要的技術目前尚處於起步階段,需要運用大量的人類智慧才能臻至成熟。我必須再重複一次古老的箴言:養育一個孩子需要一個村莊的努力,而創造一個愛因斯坦則需要數十億人的文明。而在另一方面,當人類專心致志時,他們能夠以極快的速度發展技術。人類從第一架有動力、可控制、可操縱的飛機(一九〇三年)發展到第一次登月(一九六九年),只花了不到一個人一生的時間——不過這個發展是發生在人口迅速增長的背景下。比較晚近的例子是應對新冠疫情的舉措,包括醫學創新以及對疫苗接種和免疫的更深入了解,都僅用了幾個月的時間。
接下來,在本章的剩餘部分,我將探討人類生態位在不久的將來可能出現的未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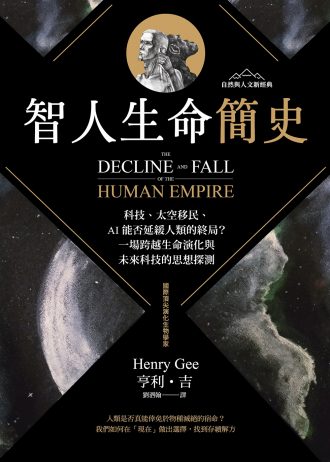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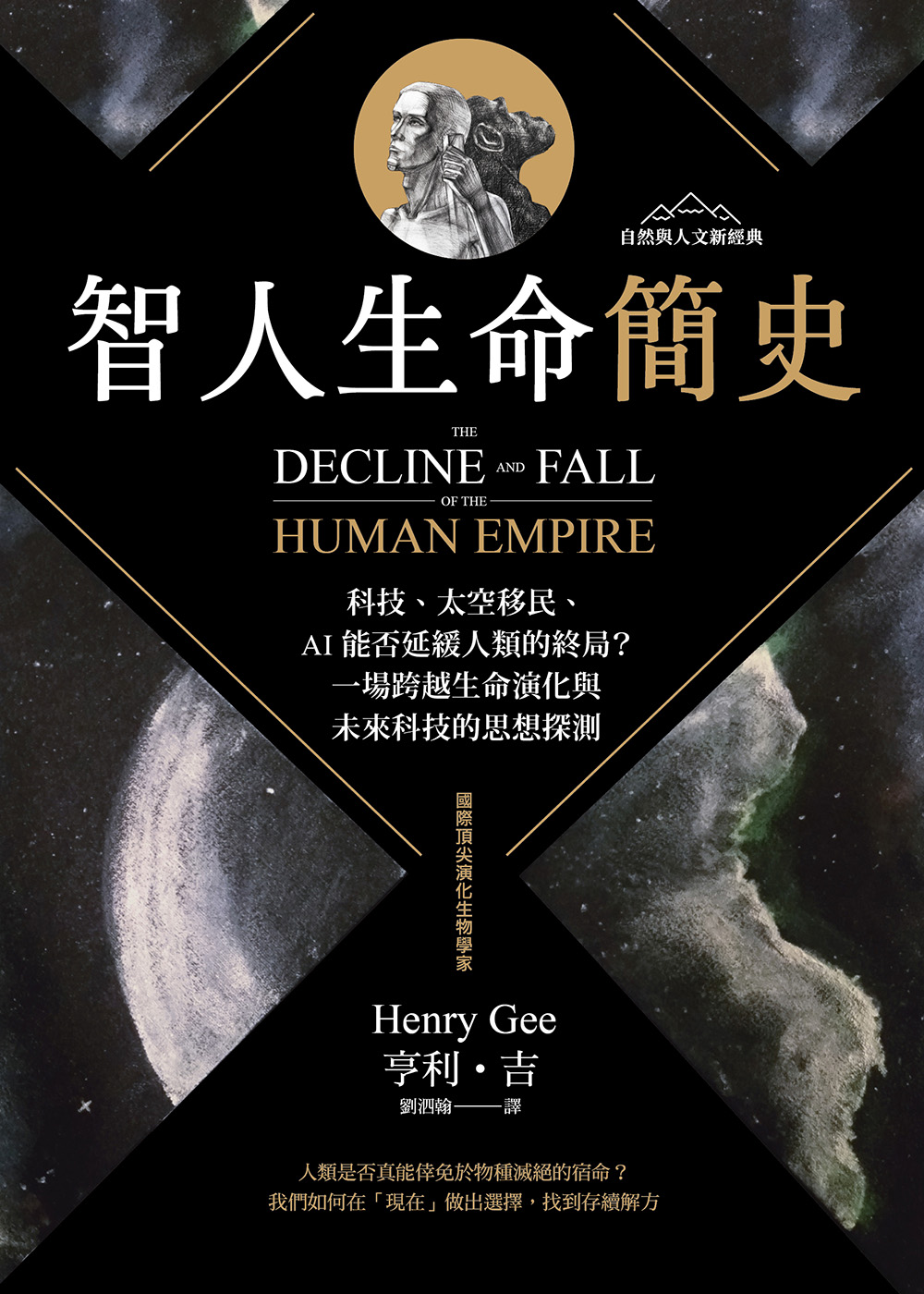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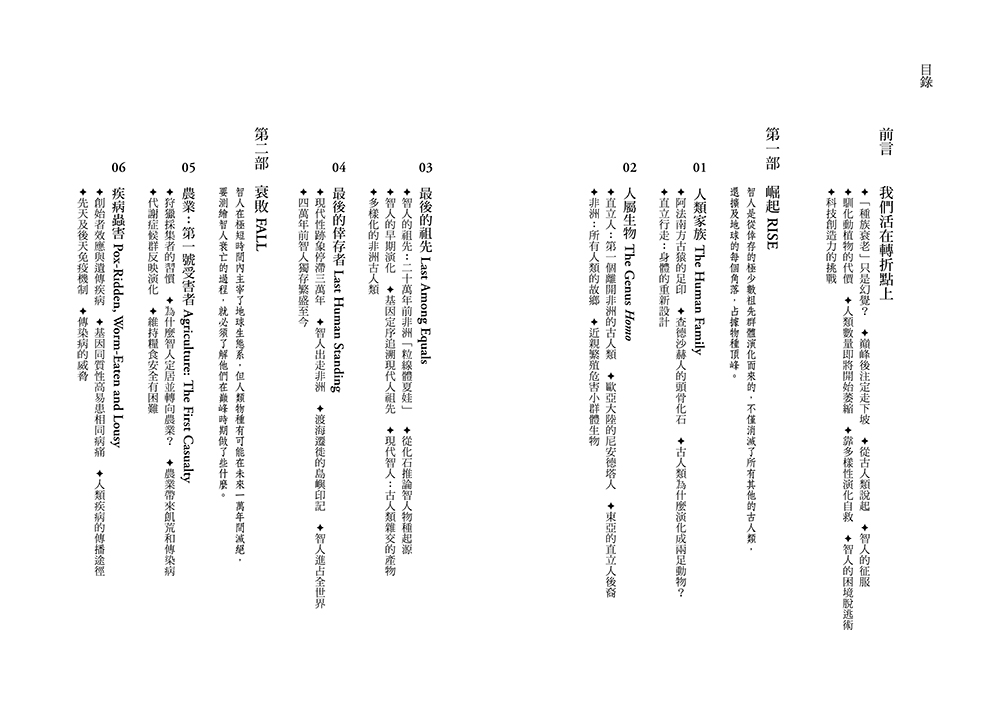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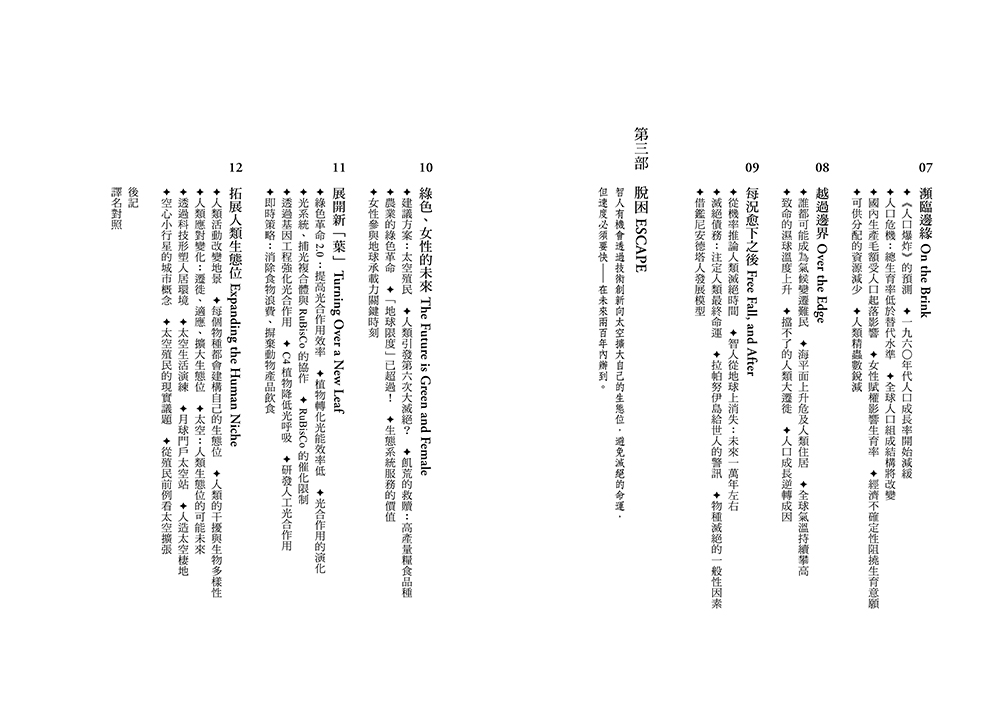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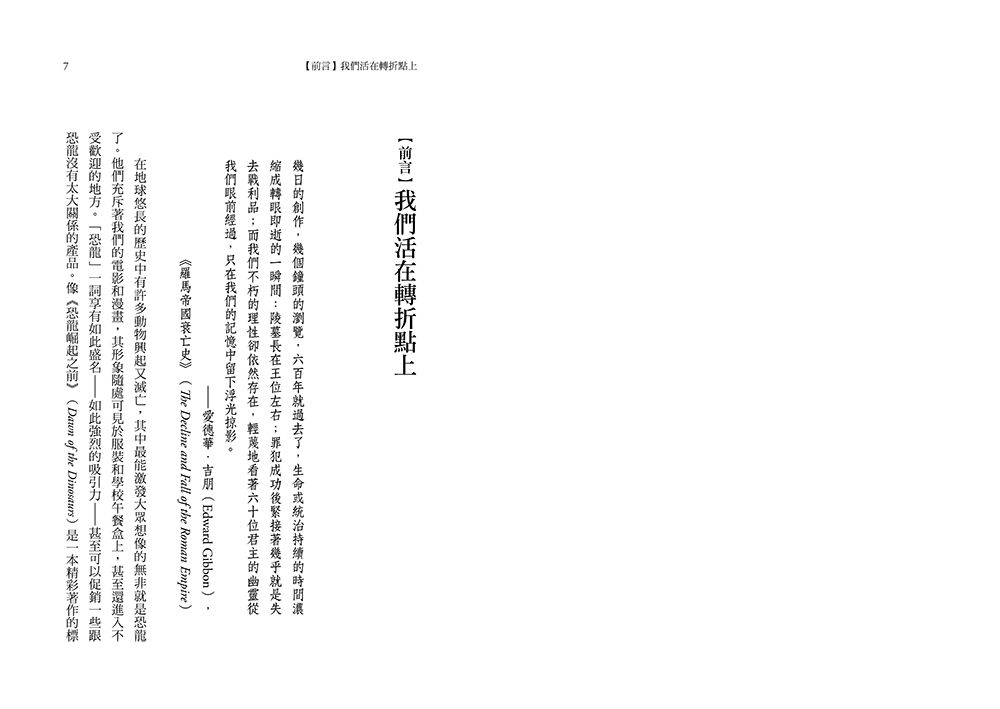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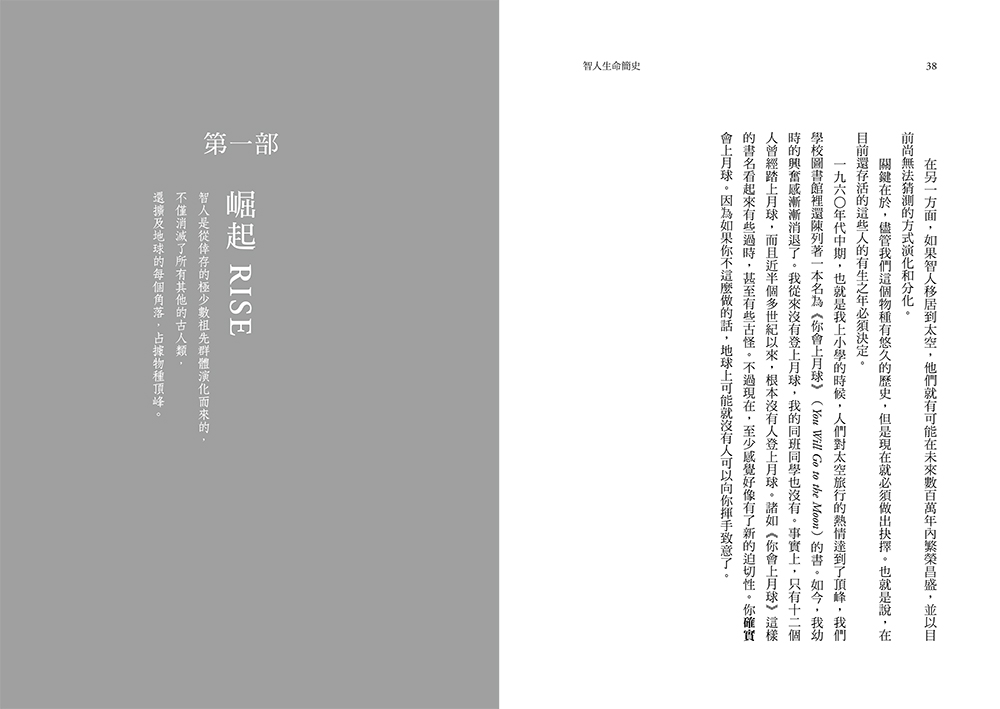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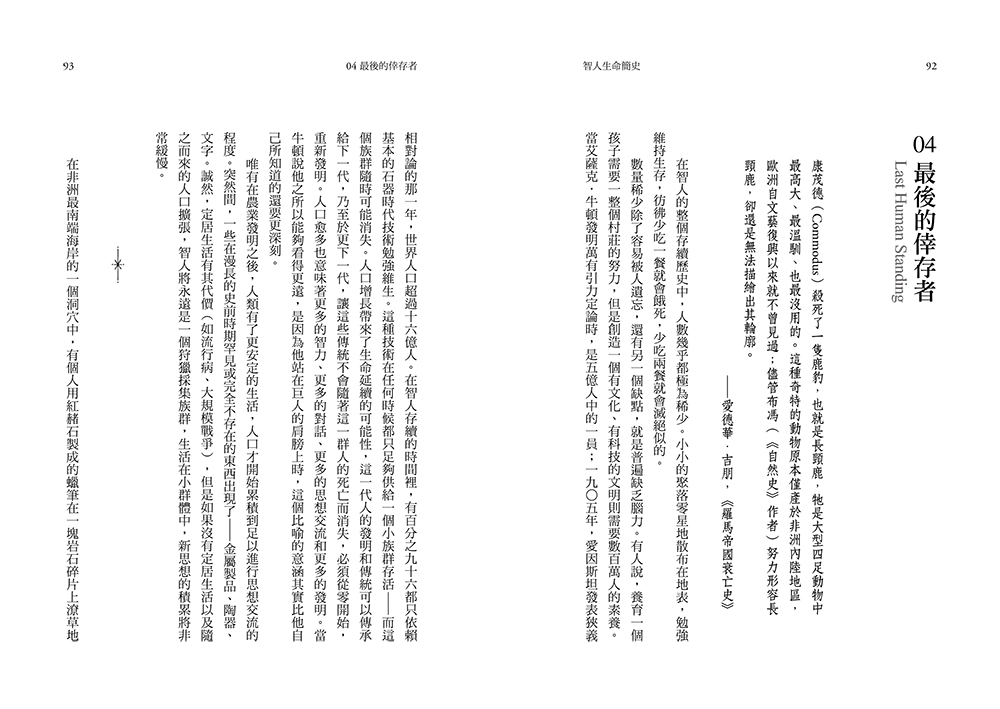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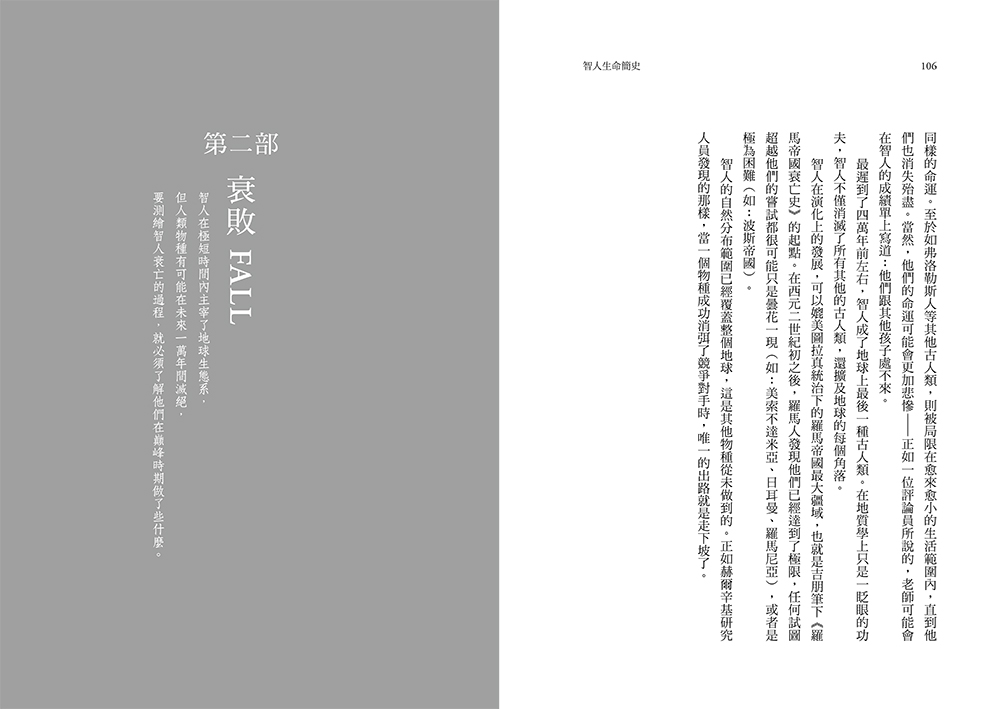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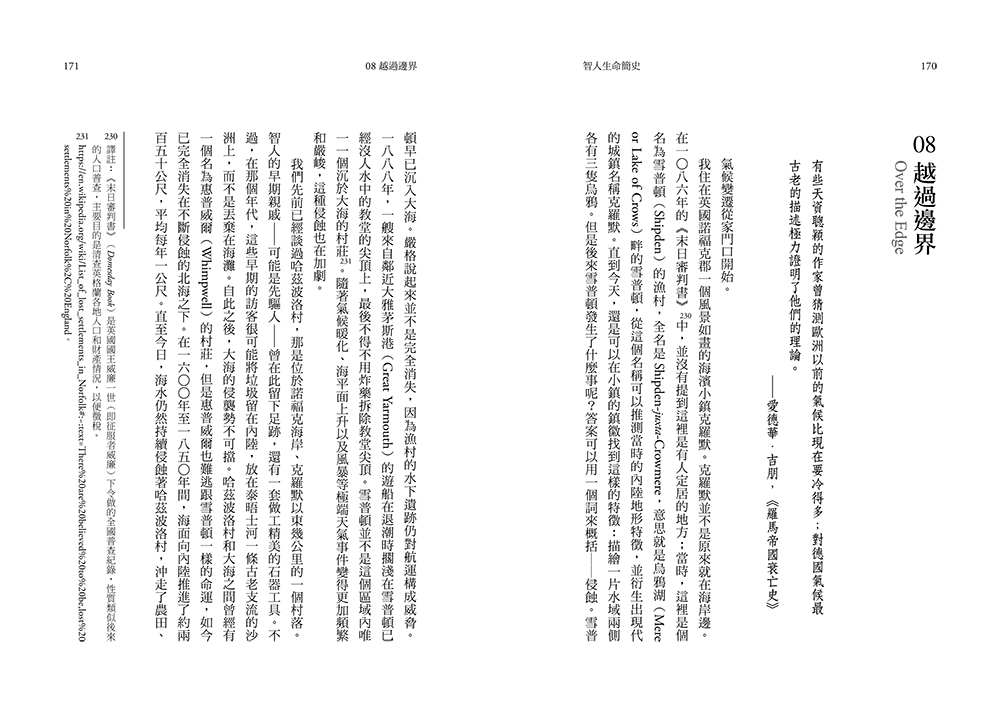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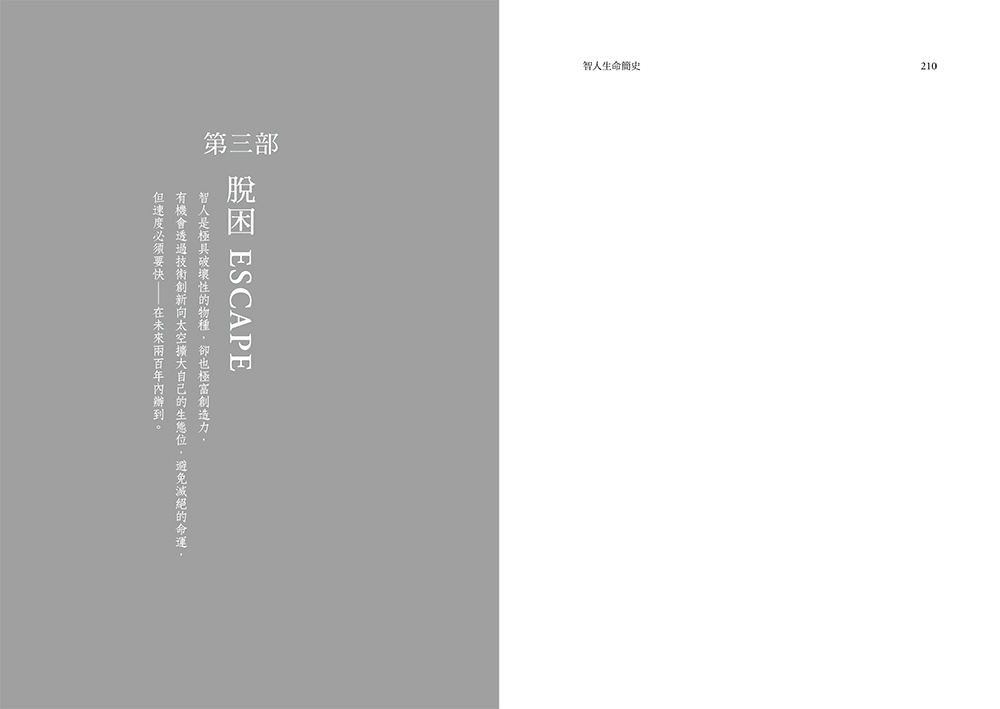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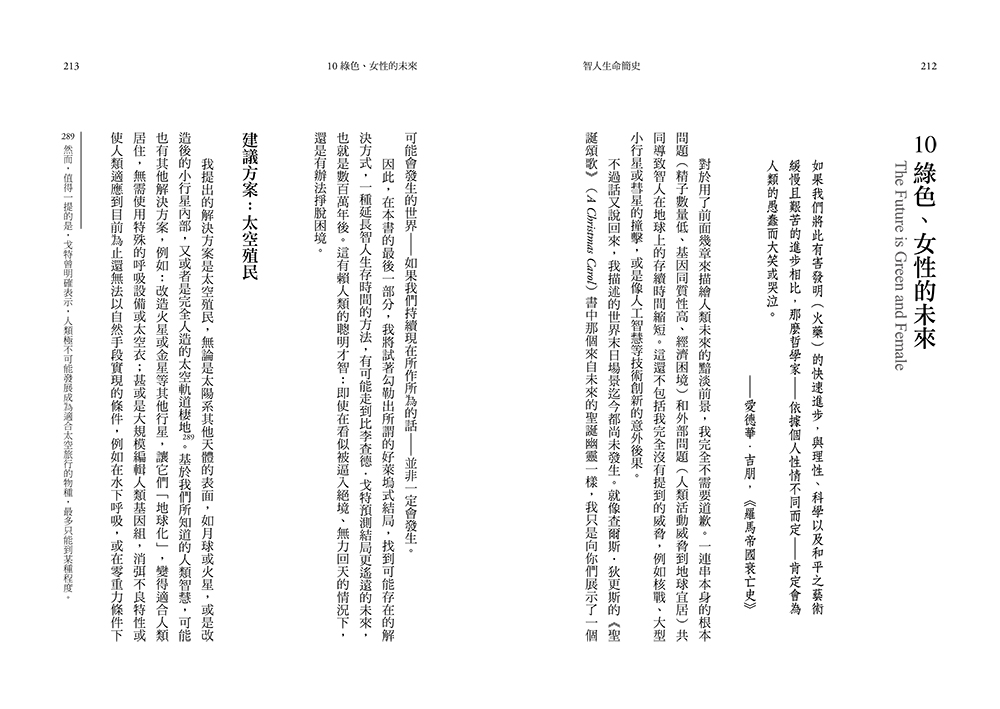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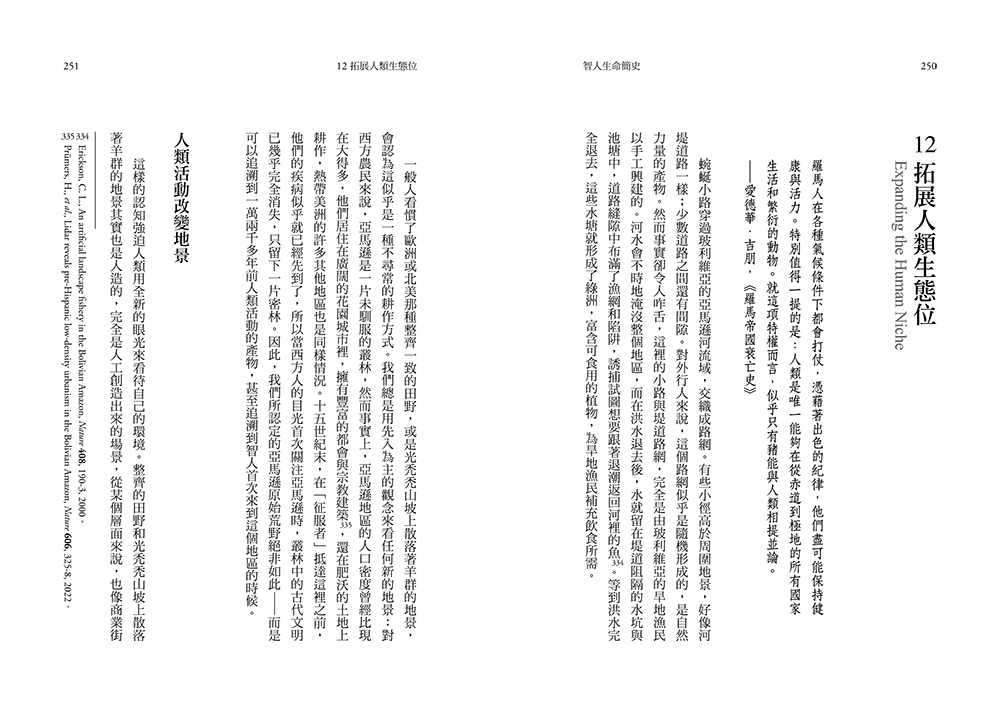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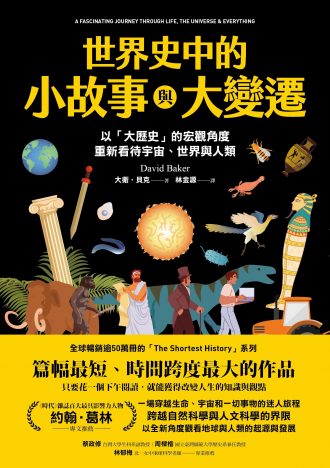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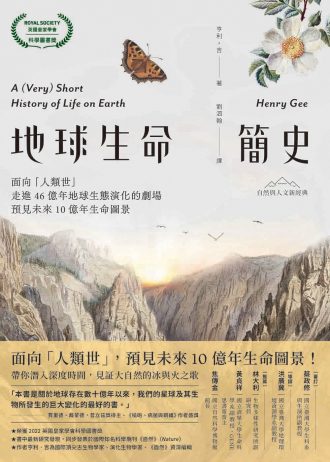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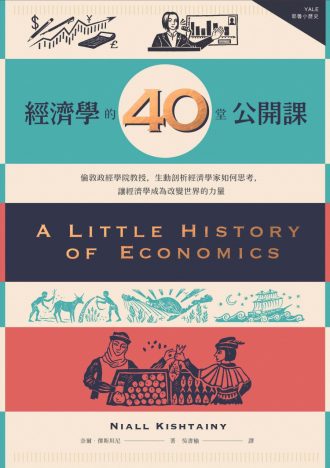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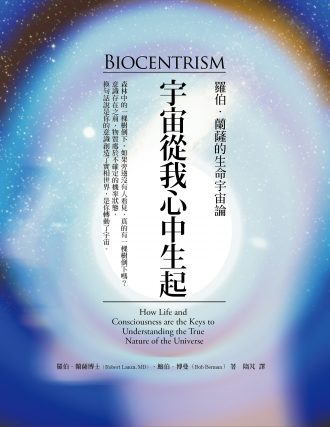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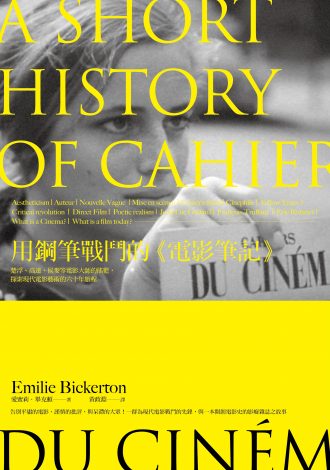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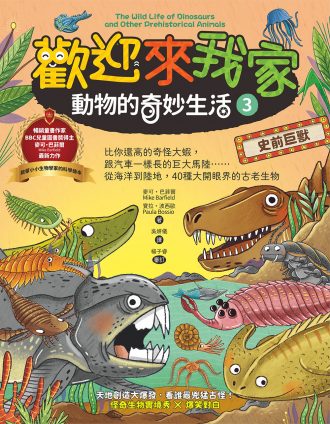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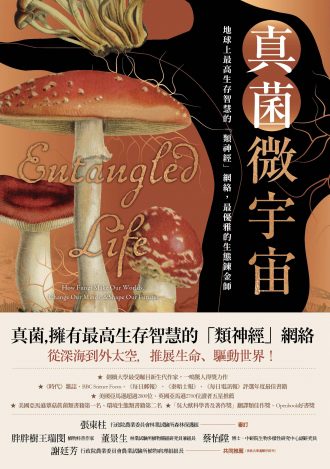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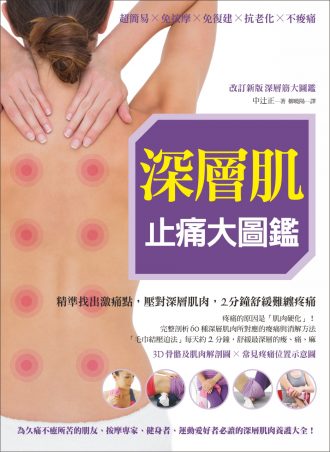
Reviews
There are no reviews y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