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連載
【以下內容摘錄自不同章節】
◎烏魯克石瓶
西元前三三○○年,在美索不達米亞(Mesopotamia)的烏魯克(Uruk)城裡,有一座供奉伊南娜(Inanna)女神的神廟,神廟裡有一個人,他是這座城市的統治者,正站在一只高高的瓶子前,凝視著瓶身上所刻的東西。
這個瓶子由雪花石膏石(alabaster stone)製成,高度超過一公尺,瓶身刻著水平帶狀的浮雕,一共有四層,上下相疊,每一層都刻滿了人物,描繪著人們如何敬神與謝神。
那位統治者由下往上順著那一圈又一圈的雕刻,開始嘗試「讀懂」瓶身所刻的故事。
瓶身最底下的波浪狀線條是潺潺的流水,水岸邊有亞麻和椰棗生長。往上一層,有閒晃的綿羊與山羊,顯示此地土壤豐饒,而此時是豐收時節。再上去一層,則是一排裸身的男性,他們扛著籃子與雙耳瓶(amphorae,一種陶罐),瓶裡裝的飲料和食物滿到都快掉出來了。來到最上層,我們終於知道這群人在做什麼了—他們帶著供品,朝著伊南娜女神的神廟邁進,準備將豐收的榮耀獻給女神。
伊南娜是烏魯克的守護神。她的子民心懷感激的獻上一籃又一籃滿溢的食物,感念她讓作物成長、牲畜健壯的恩惠。浮雕上的伊南娜站在神廟外俯瞰這一切,旁邊還站了一個披著布衣的男性。兩人站得很近,可見那名男性應該也是神明等級的人物。不過他的頭上刻著代表「能與神溝通的帝王」(Priest-King)的字,顯示他其實壽命有限。
看著看著,統治者先生笑了。他十分滿意自己被當作神,永生不死的刻在石瓶上,還站在伊南娜女神旁,好像自己也和她一樣神通廣大。
《烏魯克石瓶》(Uruk Vase)是目前已知最早的敘事藝術(narrative art)作品之一。敘事藝術的意思,就是敘說某件事的藝術,只要順著圖像的順序跟著讀,就可以看懂上面在說什麼,有點像現在的連環漫畫。史前時期的洞窟壁畫,可能就是部落的薩滿或長老說故事的依據,藉由圖像把故事說得活靈活現。到了西元前三三○○年,藝術家開始製作精緻的浮雕,用浮雕來說故事,就像《烏魯克石瓶》一樣。這樣後來的人只要自己看,就能「讀懂」上面的故事了。
⋯⋯
烏魯克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城市。在當地,藝術是用來崇敬神祇的,例如守護神伊南娜。這也正好符合統治者的心意。正如開頭的小故事所說的,《烏魯克石瓶》上那個沒有名字的「能與神溝通的帝王」,就是該城的統治者,他被刻在伊南娜身旁,當作與神同等級的人物而受到崇拜。
在這整片肥沃土地上,在遍及現今希臘和土耳其,遠至伊朗、伊拉克、印度的整個區域內,所有的藝術家也都在為貴族陵墓、神廟、宮殿等建築創作類似的作品。各個文明的統治者會聘請藝術家把神祇和自己的豐功偉業雕刻成藝術品。因為是統治者付薪水給藝術家,所以他們也一併掌握了作品的敘事立場。
——————–
◎埃及的陵墓藝術
古埃及文明跟美索不達米亞文明差不多是在同一時間開始的,兩者都持續了三千年之久。從繪畫到雕刻,埃及的藝術自始至終都毫無懸念的保持既好認又一致的風格。埃及的藝術家也和美索不達米亞一樣,不認為雕刻或繪畫就是要愈像愈好,而是要能捕捉到人物重要的特徵,無論是描繪法老還是天神,抑或在田裡工作的女子,都是如此。
當時的埃及是非常富有的國家,因此,不是只有宮殿、神廟、皇族的陵墓會裝飾得美輪美奐,例如,內芭門(Nebamun)陵墓裡中的《內芭門沼澤狩獵圖》(Nebamun Hunting in the Marshes),就是個很好的例子。
這幅壁畫完成於西元前一三五○年左右,位於底比斯(Thebes,現在的路克索〔Luxor〕)。內芭門生前是會計師,在阿蒙(Amun)神廟上班,每天都在跟穀物產量的數字打交道。在畫中,可以看到他站著在獵捕飛鳥,旁邊還有他的太太賀賽蘇(Hatshepsut),以及他的女兒。內芭門側著臉,雙腳跟臉朝著同一方向前進,但上半身和肩膀卻是正面朝著我們。他的頭也混合了兩種視角:頭部看起來明明是側臉,但左眼卻又直直盯著我們。
由此可見,埃及的藝術家是把人類最有特色的部分擷取出來,再加以重組,創造能代表人類的永生象徵,陪伴死後的人們在裝飾華美的陵墓繼續延續生命的旅程。埃及很多的藝術都是為了要在死後的世界陪伴死者而做,埃及的陵墓藝術,則更具體展現出人死後過著什麼樣的生活。這對埃及人可是至關重大的事,因此陵墓藝術特別受到重視。《內芭門沼澤狩獵圖》就顯示出內芭門先生死後想要過著跟家人一起打獵的日子,而不是繼續會計工作。
——————–
◎復刻希臘作品的羅馬雕塑
西元前二世紀時,羅馬帝國的版圖遍及整個地中海地區,當時羅馬有超過一百萬名居民,全城到處都看得到雕塑作品。
羅馬人把雕塑當成打勝仗的戰利品,每攻下一個城鎮,就會在羅馬舉辦一場叫「凱旋」的盛大遊行,秀出這些戰利品。雕刻家也會接受委託,用大理石來製作希臘雕塑的複製品,再透過海路運到羅馬。
不僅如此,許多名作的石膏模也開始四處流通,讓全羅馬帝國的藝術家都可以加入複製的行列,例如裸體的阿芙蘿黛蒂像和維納斯像,就有幾千個複製品留存至今。當時羅馬的有錢人家裡不會只放一、兩座雕塑而已,光是前廳(入口玄關)就會用好幾十個雕塑作品擺出陣仗,家中的列柱中庭(庭院)亦是如此。
隨著羅馬帝國的擴張,追溯各雕塑作品的年代變得愈來愈不容易。因為羅馬人太欣賞希臘人的生活方式,以致於人人都想擁有希臘的雕塑作品,然而作品數量有限,供不應求,因此,復刻希臘時期藝術家的舊作,或是創造新件向希臘原作致敬,都是很普遍的現象。
——————–
◎非洲的鹽臺
一五二○年之際,葡萄牙人在探索了非洲西岸又繞過了好望角後,建立了好幾條貿易路線,最遠可到印度,一五四三年時更抵達了日本。因此,這個時代的藝術品,也記錄了當時不同文化之間有什麼樣程度的交流。
一五二一年間,杜勒和費南德斯.達瑪德(Rodrigo Fernandez d’Almada)變成好友,當時達瑪德是安特衛普一名葡萄牙國際貿易祕書。他花了三個弗洛林幣(相當於現在的五百英磅),向達瑪德買了幾件非洲藝術品,那是兩個來自獅子山(Sierra Leone)的象牙鹽臺(saltcellar)。(以下是當時其他作品的價格,提供對照:杜勒之前用兩個弗洛林幣買到霍倫布特的袖珍畫,而他自己的小型畫作,一張也差不多這個價錢。)
由薩皮族(Sapi)雕刻家製作的鹽臺,早在進口到安特衛普這個歐洲北方國際貿易中心販售的幾十年前,就已開始賣給葡萄牙人了。藝術家在製作這些鹽臺時,必須把象牙刻得很深,才有辦法在刻出一個球狀容器—就是裝鹽的地方—後,下方還刻了一群小人支撐著這個球體。雕琢如此精緻的鹽臺不是為了當成器皿使用,而是用來觀看、欣賞的藝術品。
隨著葡萄牙與非洲西部之間的交流愈來愈密切,更促成了一種混搭雙方元素的「非葡」鹽臺的出現。這秊鹽臺上同時雕有非洲的男人、女人、動物,但也有葡萄牙的商人、士兵、船隻、聖經故事的橋段。即使如今製作這些鹽臺的藝術家姓名已不可考,但仍可看出他們的雕刻技巧有多麼精湛,適應新客戶、新需求的速度有多快。這些藝術家參考歐洲的祈禱書及旅遊日誌中的版畫作品,創造出融合了兩種文化的新風格。
——————–
◎巴洛克畫家卡拉瓦喬與卡拉契
即將跨入十七世紀之際,羅馬藝術人才濟濟,如百花齊放。為什麼到了這個時候,還有這麼多藝術家搬到羅馬?那是因為天主教教會再次壯大,擁有超深的口袋和超大的委託案,吸引他們來到這裡。還有不少藝術家從歐洲各地來到這裡研究古典藝術,研習文藝復興時期才華洋溢的米開朗基羅與拉斐爾的作品。
在羅馬,藝術家之間相互競逐委託案,或是為同一個地方創作,就地直接以作品一較高下。例如,一六〇〇年七月,卡拉契接受委託,為人民聖母堂(Santa Maria del Popolo)的提伯黎歐.切拉西禮拜堂(Tiberio Cerasi’s chapel)的禮拜堂天花板繪製濕壁畫,並為聖壇繪製聖壇畫。
兩個月後,當時教宗的財政部長—富有的律師切拉西(Cerasi),又找了卡拉瓦喬來畫預計掛在同一座聖壇兩側的作品。
卡拉契的聖壇畫《聖母升天圖》(The Assumption of the Virgin),是一幅描繪和諧片刻的曠世之作。畫中聖母張開雙臂,即將升上天堂,天使也在身旁簇擁著她,她的身後襯著神聖的金色光暈。當人們走進禮拜堂,可以感覺到她好像是張開雙手在歡迎我們似的。
兩旁牆上的卡拉瓦喬作品,則與這幅畫形成強烈的對比。畫面的主調不再是卡拉契那超然神聖的藍、紅、金色,而是卡拉瓦喬那屬於人間凡俗的棕、白、赭等大地色。為了在《聖母升天圖》旁爭取觀眾的目光,卡拉瓦喬以閃耀的紅來吸引我們的注意力。
⋯⋯
如今,我們將卡拉契和卡拉瓦喬兩位都稱為巴洛克風格的藝術家。巴洛克是一個統稱十七世紀各種藝術的詞彙,指的是畫面充滿戲劇性,人物充滿動態感,卡拉瓦喬激昂的畫作就是典型。
不過在當時義大利新興的藝術學院裡,教的主要還是卡拉契的古典路線,也就是以古代雕塑、希臘神話、文藝復興為基礎的創作風格。早期描寫藝術作品的寫作者同樣偏好卡拉契的理想主義,而非卡拉瓦喬驚世駭俗的寫實主義,因此之後的三百年間,藝術學校的學生都還是以卡拉契的風格當作對自我的期許。
——————–
◎克林特:罕為人知的抽象藝術先驅
儘管這些藝術家自認站在西方抽象藝術尖端,不過大概早在他們十年之前,瑞典藝術家克林特(Hilma af Klint,1862- 1944)就創作了具神祕氛圍的巨幅抽象畫,畫面充滿流動的線條、螺旋、如蛋般的橢圓形,也有像標靶或三稜鏡等圖案。
一九○六至一九一五年間,克林特以近兩百幅名為「為神殿而作的油畫」的系列作品,探索靈性、科學、藝術生活等廣泛面向。其中一九一五年的《一號聖壇畫》(Altarpiece No. 1),即是她用來讚揚繪畫本身的作品。畫中我們可以看到多種漸層的色彩層層相疊,以類似金字塔的形狀向上升起,最上方則是一個有紫色光冠的金色球體。
克林特生前不曾公開這個系列。因為她本身也是靈媒,在降靈會與她對話的聖靈說服她,這系列畫作對世界來說太過前衛,人們無法了解,於是克林特訂出明確時間,這些作品在她死後二十年才能公開。事實上,這個系列直到二十一世紀才普遍受到認可。
相較之下,與她同時代的男性藝術家都在發表抽象作品後,藝術生涯扶搖直上,也在後來的藝術史中為自己占據了一席之地。
——————–
◎二戰後的澳洲藝術
英國於一七八八年開始殖民澳洲,但在那之前,澳洲原住民與托雷斯海峽島民(Aboriginal and Torres Strait Islander)已在這塊大陸生活了超過五萬年。他們的藝術在數千數萬年間演化,不同部族都發展出各自獨特的圖騰。
這些圖騰一開始是畫在懸崖岩壁上,或是遮風避雨的場所裡,後來也用在具儀式性的身體藝術當中,或是畫在沙地,成為非永久的大型地板畫。圖騰中的螺旋、圓圈、線條,與似乎能和生命一同脈動的無數點點交織在一起。澳洲的原住民相信他們屬於大地,這與西方認為大地屬於人類的觀點相反。對澳洲原住民來說,人是要和土地融為一體的,而非宣稱自己擁有這片土地。這些畫作在西方人眼裡看來顯得抽象,事實上,這些作品一如他們的創世神話,都根植於人和大地之間的緊密連結,而這樣的連結狀態,如今被稱為「傳命」(the Dreaming)。
一九三○至一九四○年代,藝術家普雷斯頓(Margaret Preston,1875-1963)極力推動將原住民藝術認可為澳洲真正的藝術資產。普雷斯頓住在雪梨,但拒絕接受雪梨藝術圈「把殖民者的藝術置於被殖民者的藝術之上」的主流觀點。她拜訪了許多原住民聚落,認為澳洲在建立國族認同時,原住民的作品才應該是「澳洲藝術」的核心。普雷斯頓也汲取不同文化的觀點,在自己作品中融入了澳洲原住民、亞洲、歐洲等地藝術,創作了生氣盎然的風景畫,創作於一九四二年的《飛越肖爾黑文河》(Flying over the Shoalhaven River)就是其中之一。
普雷斯頓致力提升原住民藝術地位時,也出現了一些受過西方藝術訓練的原住民藝術家。
納馬吉拉(Albert Namatjira,1902-1959)以遼闊的水彩風景畫,展現澳大利亞焦黃的內陸景色,同時也證明這樣的作品非常受歡迎。不過要到一九七○年代,才開始有藝術家在畫布上畫出傳統的原住民藝術,進而傳播到世界各地。
——————–
◎巴斯奇亞與哈林
報紙《村聲》(Village Voice)稱「時代廣場展」是「一九八○年代第一場激進的藝術展覽」。這場展覽讓巴斯奇亞和哈林兩人的藝術生涯扶搖直上,一年之內,這兩位年輕藝術家成了大名人,卻也走完英年早逝的一生。
巴斯奇亞十五歲就離家,睡在紐約東村(East Village)朋友家的沙發上。他用噴漆、油畫棒、壓克力顏料繪製動態感十足的大型作品,內容融合多種元素,有街頭塗鴉,也有美國抽象畫風,有課本會看到的那種解剖圖,也有黑人文化、爵士、嘻哈等。
一九八二年,他舉辦第一場個人展覽,所有作品全部售罄,這一年也是他和巨星瑪丹娜交往的那一年。隔年,他和沃荷變成很好的朋友。
巴斯奇亞的作品有一種粗狂的力量,捕捉了一九八○年代紐約的混亂奔放,生活在夜店、跳舞、塗鴉、毒品中的樣態。他在二十七歲時因過量海洛因而離世,不過他留下的作品仍以其耀眼的活力,使藏家趨之若鶩,例如一九八二年的《無題》(Untitled),也就是有黑色類骷髏頭的那件作品,最近才在拍賣場以一億一千萬美元的高價售出。
相較之下,哈林的成長背景就顯得保守許多。他在美國賓州長大,一九七八年搬到紐約念書才接觸到塗鴉藝術。
「時代廣場展」結束不久的某一天,他在欣賞地鐵車廂上的塗鴉時,突然「靈光乍現」。他發現地鐵站中的廣告看板在新舊廣告更換之間,會放上黑色的平光紙。這紙看起來有點像黑板,是可以拿來畫畫的空白平面。於是他跑上階梯,買了白色粉筆,又跑下來,在短短一分鐘之內創作了他第一件街頭藝術作品。
接下來的五年,哈林在整個紐約地鐵中畫滿他卡通式的人物。這些人物在擁抱、在親吻、在跳舞、在玩呼拉圈,他以此表達自己對愛與死亡的想法,對性與戰爭的觀點。哈林希望自己的作品存在於街頭,因為這樣所有人都看得到。他表示:「你不需要任何與藝術有關的知識,就可以看、可以欣賞我的塗鴉。這些塗鴉裡沒有什麼祕密,也沒有什麼需要理解的事。」
哈林後來成為名人,也成為同志的偶像。一九八○年代,愛滋病的蔓延重重打擊了同志社群,哈林從不怯於透過藝術來表達他對愛滋的看法。一九九○年,他因愛滋相關疾病過世。
——————–
◎以攝影扣問真實
另外也有些藝術家運用攝影來質疑攝影本身記錄「真相」的能力,嘉德里安(Shadi Ghadirian,1974-)一九九八年創作的「卡札爾」(Qajar)系列,就是這樣的作品。
她在攝影棚裡復刻十九世紀伊朗人像攝影師會拍攝的那種肖像照:把拍攝背景繪製成當時的風格,讓照片中的女性穿上復古的服裝,同時再搭配一些道具。然而,她使用的道具都是當代伊朗女性才有辦法接觸到的東西,例如手提式卡帶收錄音機、吸塵器等,有些照片中的女性還騎著腳踏車、戴著太陽眼鏡、喝著罐裝的百事可樂,可見她們並不是真的生活在十九世紀。
嘉德里安現在仍住在伊朗,藝術家娜霞(Shirin Neshat,1957-)則已流亡到海外,但她們的作品都運用了後殖民與女性主義理論,來探討在伊朗境內與境外的伊朗女性是如何被觀看的。
娜霞在一九九三至一九九七年間創作的「阿拉的女人」(Woman of Allah)系列作品,拍攝了包含她本人在內的女性肖像照。照片中的女性戴著頭巾,拿著槍,臉上則以波斯文寫滿殉道詩歌和女權文字。對大多數看不懂波斯文的西方觀眾來說,那些從臉頰蔓延至下巴的激進詩詞,更像是一種猶如書法的密語。
這個系列中的《反抗的沉默》(Rebellious Silence),觀看者亦無法確認照片中手持來福槍的女子究竟是要殺人,還是在自衛。那些文字遮蓋著她臉龐,似乎暗示著她是一名殉道者。不過,真的是這樣嗎?還是,她其實是受害者?這些影像如此複雜,不禁使我們自問:我們看見了什麼?這些影像也讓我們意識到:照片中伊朗女性的生活與生命,並不是那麼容易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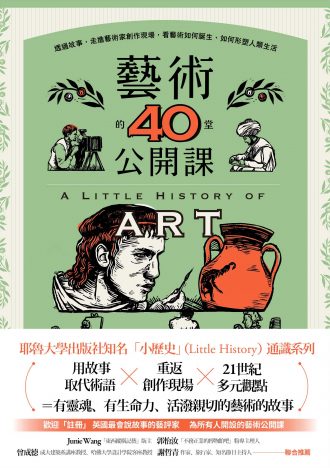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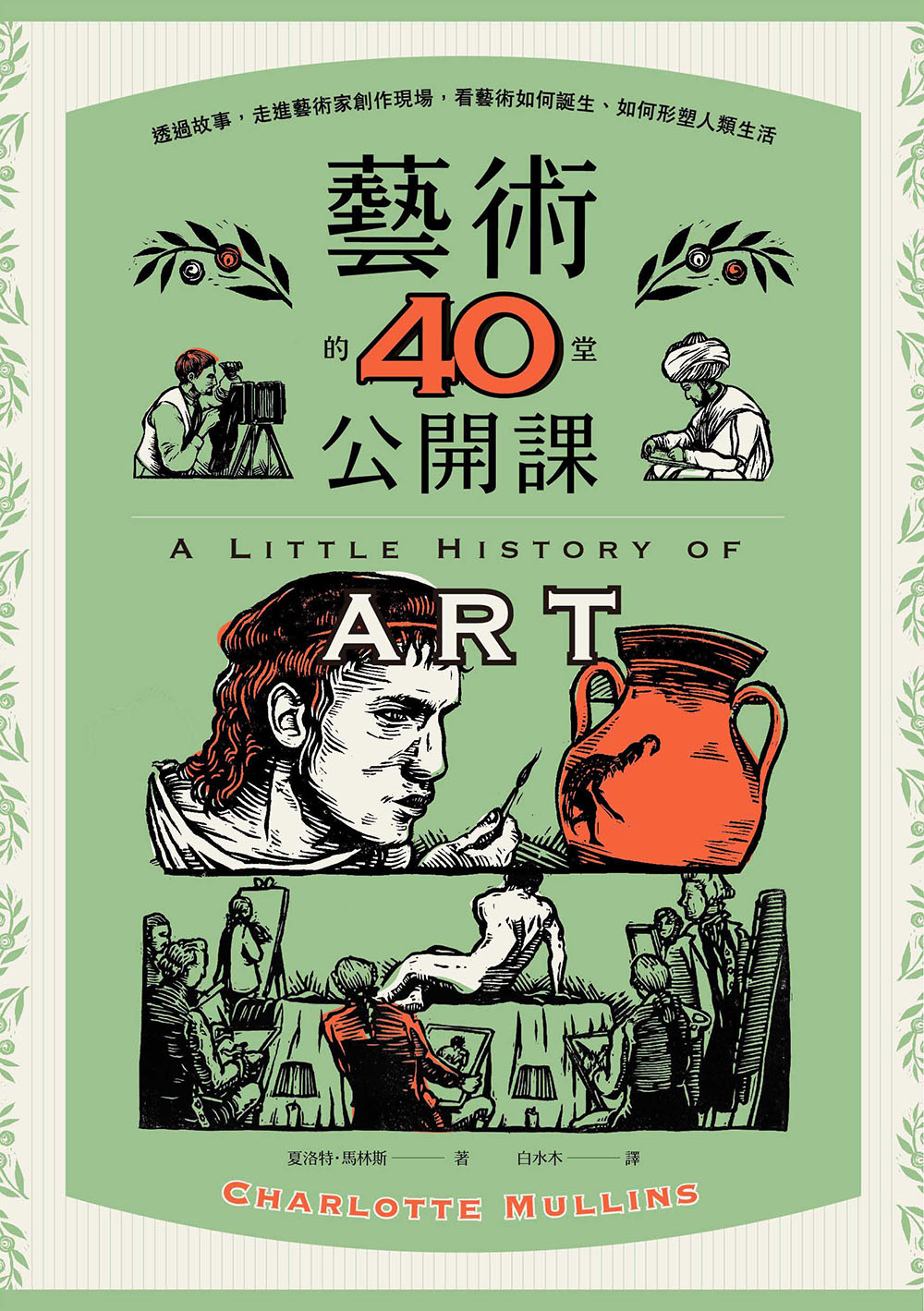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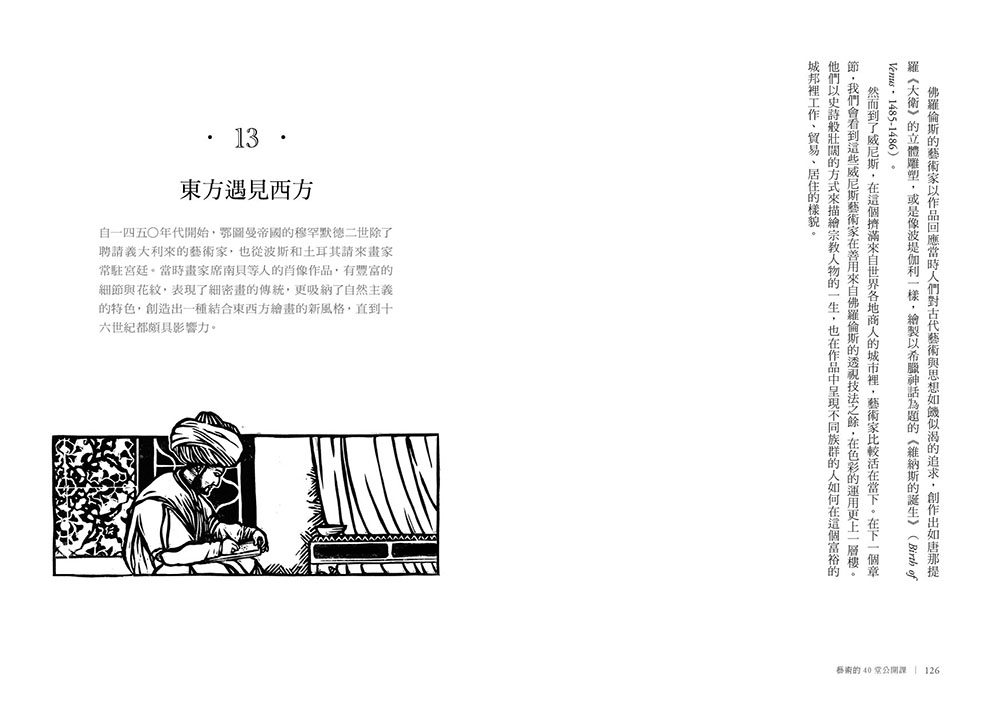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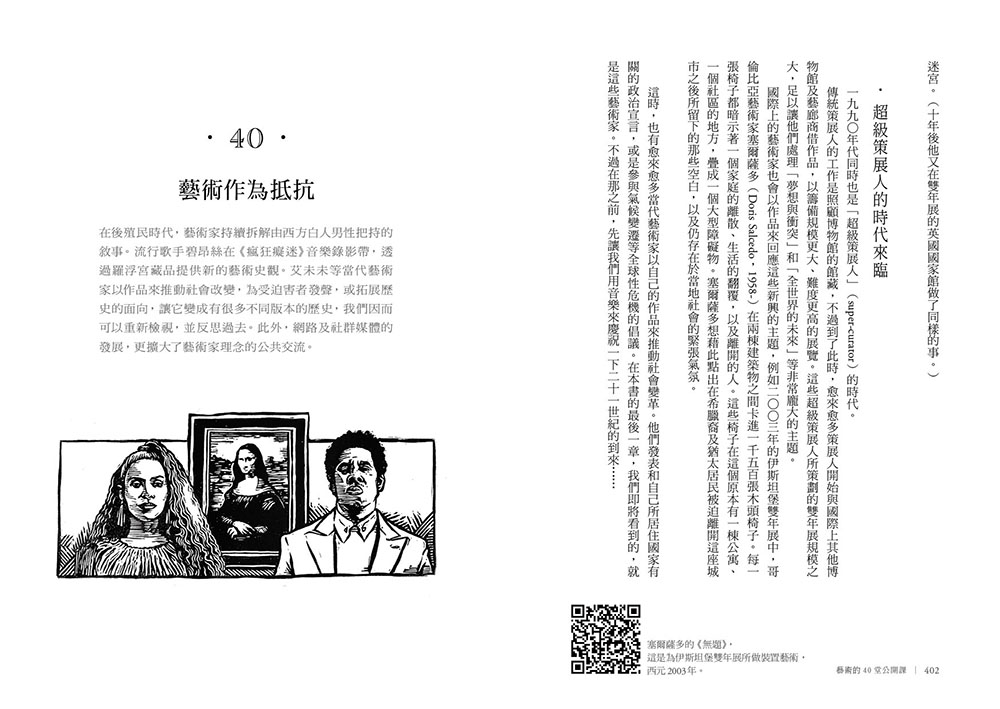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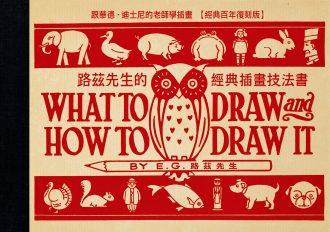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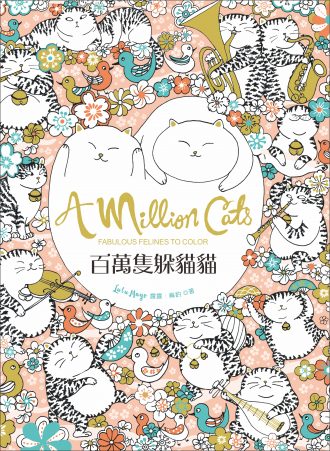


-330x474.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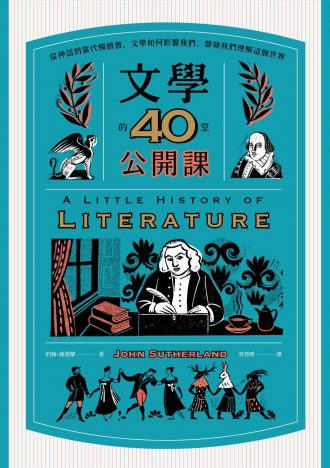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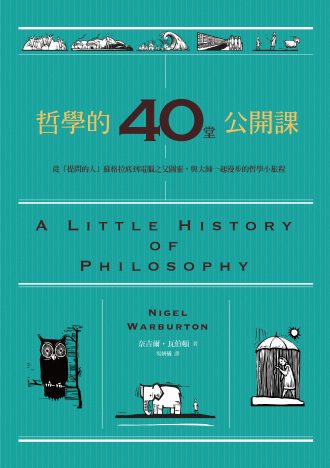




Reviews
There are no reviews y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