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驅逐出境與暈眩
1
二○○五年十二月的某一天,我在上海浦東機場的購票櫃檯買了一張飛回首爾的單程票。經驗豐富的旅客一定不會在機場買機票,更不要說是單程票了,因為單程票貴得離譜。但當時的我卻沒有選擇的餘地,因為我就要被驅逐出境了。
「您是付信用卡,還是現金呢?」
出於職業的好奇心,我在這嚴肅的瞬間,面對這種微不足道的問題,以及那奇妙的效果展開了思考。比如,我們可以問去刑場的死囚。您是想走樓梯,還是想搭電梯呢?人類受到的訓練是有問必答,因此在死到臨頭的瞬間,還是會稍稍苦惱一下,進而暫時忘卻眼下真正將要面對的問題。雖然我的錢包裡有人民幣,但我還是選擇付了信用卡。據研究表明,付現金會刺激我們大腦中感受痛苦的區域。因為就算是自己主動把錢交給對方,還是會有一種遭到掠奪的感覺。但付信用卡則不同,信用卡從我們的錢包裡抽出來,只是暫時交給對方,很快就會還回來。現金給出去後,可就有去無回囉。雖然明知道這是在自欺欺人,但我不想再對持續進化的大腦提出更多的要求了。我遞出信用卡付了回韓國的單程票後,忽然覺得自己可以理直氣壯地面對站在身旁的公安了,這稍稍減輕了我遭遇驅逐出境的痛苦。我所持有的信用卡付款成功,這說明我在本國的信用沒有問題。這似乎足以證明我是一個不應該受到如此待遇的人,但不管我自己怎麼想,公安根本不在乎我的支付能力。我們直接進入了下一個步驟。公安帶領我穿過工作人員的專用通道,做了形式上的X光安檢,最後抵達登機口。之後的兩個小時,我沉默不語地坐在登機口前的椅子上,等待飛往仁川的航班開放登機。
從浦東機場起飛的飛機經由東海上空,降落在了夜幕降臨的仁川機場。我拿到行李後,給妻子打了電話。
「你在哪兒?到住處了嗎?」
「沒有,我在仁川機場。」
妻子一時啞口無言。她感到吃驚,這實屬正常,因為早上剛出國的丈夫,晚上就回國了。我原本的計畫是去一個月。
「你沒去嗎?」
「去是去了⋯⋯」
「出了什麼事?你哪裡不舒服?」
「沒有,是我⋯⋯我、我被驅逐出境了。」
那段時間,我在大學任教,整個學期根本寫不出小說。所以我打算趁放寒假的時候專心創作,於是尋找起了適當的工作地點。很多韓國人在上海浦東經營民宿,他們以投資為目的買下公寓,淡季的時候會短期租給觀光客,而且還提供一日三餐。我心想,到了那邊有吃有住,非常適合寫作。無聊的話,還可以到上海市區逛一逛。我寫了一封郵件給房東,對方很快回信說,必須將全額費用匯到中國工商銀行才算完成訂房。回信裡還提到,公寓是新建的,所以環境清潔。我預訂的客房不僅附廁所,還有視野極佳的露臺。看照片確實非常豪華,於是我把一個月的房租和餐飲費全部換算成人民幣匯了過去。我帶上準備好的資料和無聊時打算看的書。因為是冬天,加上是長期旅行,所以行李的體積非常大。但我就這樣拖著這些行李,不到一天的時間就回來了。
聽到驅逐出境這個詞時,妻子猜測這跟我寫的小說有關。因為那本小說寫的是北韓派往南韓的間諜在被祖國遺忘後,為了生存獨自求生的故事。後來這個故事以《光之帝國》的書名出版,小說藉由經歷過南、北韓生活的主人翁批判了兩種社會體制。正因為這樣,妻子才會覺得對北韓問題敏感的中國當局阻止了我入境。妻子的這種猜測並非荒唐無稽,因為後來美國、法國、德國和日本等國家都出版了《光之帝國》的翻譯版,唯獨中國的出版社傳來消息說,這種題材很難通過當局的審核(現已出版)。
但我在浦東機場遭遇驅逐出境的原因,不是因為東北亞微妙的國際形勢問題,而是我沒有做好跨國旅行時該做的最基本準備。排隊等待入境安檢時,我看到一起下飛機的韓國人手上都拿著護照和一張白紙。一種不祥的預感油然而生。
「請問,那張白紙是什麼?」
「這個?是簽證啊。」
「嗯?中國也需要簽證嗎?」
「需要吧,我們整個團都辦了簽證。」
「中國跟我們交流那麼頻繁,怎麼還需要簽證呢?」
「誰說不是,但好像真的要有簽證喔。」
我環視周圍一圈,看到一個公安。他就像剛從冬眠中甦醒過來的熊一樣,一臉懶洋洋的樣子。我脫離隊伍,朝他走了過去。因為我不會講中文,所以用英語問他:
「我是韓國人,我需要簽證嗎?」
公安面帶微笑,打了個手勢教我跟他走。我腦海裡浮現出可以辦理落地簽的東南亞國家,於是衝著走在前面的公安問說:
「這裡可以直接辦落地簽吧?」
公安連連點頭,臉上不失笑容。我跟著他走過一條長長的、沒有窗戶的走廊,迎面而來的人手裡都握有一個保溫瓶。大家經過我們時,都跟他打了聲招呼。我們走進熙熙攘攘的辦公室,公安示意我坐在角落的椅子上。空氣裡混雜著中國茶葉的味道和地下室長年不通風的霉味。公安跟我要了護照,仔細檢查了一番後拿去複印,然又後遞給我一張紙和一隻筆,要我在上面簽名。紙上寫的都是中國的簡體字,我剛落筆簽了名,他便露出燦爛的笑容拿走了紙筆。不管我問什麼問題,他都是笑著一直重複「好、好」兩個字。從這種友好的氣氛來看,彷彿落地簽很快就能辦好一樣。但是,所有的簽證都需要手續費,他卻沒有跟我提錢,我略感不安了起來。公安左手拿著那張紙,拉著我開始往外走。我還以為他會把我送到入境查驗櫃檯,但沒想我們出來的地方竟然是出境大廳。當他把我帶到東方航空售票櫃檯前時,我這才覺得事有不妙。我問這個公安熊叔這到底是怎麼回事?他用手指了指我簽過名的紙上的幾行字,雖然是簡體字,但有些漢字還是可以看得懂。內容大致是,我違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法律,因此同意在最短的時間內離境。這個公安熊叔之所以一直保持笑容,是因為我沒有惹是生非,爽快地在離境同意書上簽了名。為了節省機票錢,我問他可不可以使用預定的回程機票,他說來時的飛機已經起飛了。我又問他能不能在機場過一夜,明天再搭那班航班回國。他堅定地搖了搖頭,把那張紙塞給我看,意思是說我已經在儘快離開中國領土的同意書上簽了名。他還教我不必擔心,說會把我的行李送上飛機。
我們抵達登機口後再也沒有講過一句話。很少有人經歷過這種事,有過經驗後,我覺得心情沒有那麼糟糕透頂。這趟旅行沒有任何收穫,一天就結束了。我買了比來回機票還要貴的單程票,預先支付的房租和餐飲費可能也都有去無回(實際上沒有退款),而且有生以來第一次成為驅逐出境者坐在候機室裡。但對我而言,這都是非常珍貴的經驗。身為小說家的我有一種預感,有朝一日會把這件事寫出來。
從這點意義上看,作家的旅行或許不需要嚴謹的計畫。因為旅行過於順利的話,日後便沒有可寫的東西了。正因為如此,我去任何國家都不會在餐廳選餐時煞費苦心。運氣好的話,就能吃上美味佳餚;踩到地雷的話,就把它寫出來。不過因為我這種馬馬虎虎亂點餐的習慣,的確連累過同行的人。有一次,我和幾位作家一起到波蘭參加文學活動。在駐華沙韓國大使邀請的晚宴上,我跟往常一樣隨便選好以後就把菜單闔上了。幾位作家說要跟我選一樣的菜單,但我阻止了他們,我說我也是第一次來波蘭,對這裡的食物並不了解。但有幾位作家還是堅持了自己最初的選擇,就這樣我們剩下了一半來歷不明的食物,結束了晚餐。
當然,我也有不想冒險,只希望填飽肚子的時候。在語言不通的國家,為了躲避像是雞冠(法國和義大利)、炸蜘蛛(柬埔寨)、蝙蝠濃湯(印尼)等料理,我會這樣做。因為菜單的空間有限,所以假設餐廳不會隨便製作菜單,如果是一家老店的話,一定會遵循世界共同的規則。餐廳老闆或主廚會先把菜單分成三大類,前菜、主菜和甜品,然後每類裡會選定四、五道菜。由於印刷後便無法更改,所以他們一定會很慎重地做出選擇。排在最前面的一定是主廚最拿手、客人最喜歡的,越往下面越是不能隨便亂選的、高難度的、大膽的料理。如果你想嘗試鴿子肉(埃及)或是鯉魚魚鰾(中國)等食材烹飪的特色料理,那大可從最下面開始挑選了。廚師一定要把這些具有挑戰性的料理加入菜單的原因,是希望滿足每位客人的喜好,但也有凸顯自己餐廳特色、炫耀自己實力的目的。這就好比古典音樂演奏家在編排曲目時,會選擇像是韋瓦第的《四季》和蕭邦的《夜曲》等大眾熟悉的曲目,但也有相反的情況。
如果希望避免點餐失敗的話,最好從所有分類的最上面開始選,食材選雞肉最為安全。不管外表塗了什麼、如何醃製,裡面都會是我們熟悉的雞肉。但如果你想以旅行為素材寫點什麼的話,那就要從最下面開始選了。有時,同行的人中會跟你選擇一樣的菜單,然後對於印象深刻的失敗體驗,有的人會一直提起這件事,有的人則會把它寫出來。大部分的遊記都是由作者經歷過的各種失敗構成的。假如有一本遊記寫的都是完美實現計畫的內容,那我可能不會去看,因為肯定會很無聊。
2
既然如此,那遊記的本質又是什麼呢?踏上旅途的主人翁懷揣著旅行成功的目的,但在經歷過大大小小的考驗後,卻收穫了與最初的目的相反的什麼,然後返回到原點。馬可.波羅帶著跟中國做貿易、掙大錢的目標踏上了旅途,但世界跟自己想像的截然不同,他醒悟到世界上存在著多種多樣的人類和動物、文化和制度,於是回來後寫下了《東方見聞錄》。
旅行見聞可以說是人類最久遠的故事型態。主人翁總是會到很遠的地方去。羅納德.B.托比亞斯(Ronald B. Tobias)在《經典情節20種》(20 Master Plots)中把「探尋情節」介紹為世上最久遠的一種情節。主人翁為了探尋什麼踏上旅途,而探尋的對象一般都是他可以賭上整個人生的什麼。
在美索不達米亞挖掘出的《吉爾伽美什史詩》(Epic of Gilgamesh)中,主人翁吉爾伽美什為了探尋永生的祕訣,踏上旅途。同樣是很久遠的故事中,奧德修斯在結束特洛伊戰爭後,返回妻子和兒子所在的故鄉,一路上歷經險阻,但他始終沒有放棄。探尋情節最有趣的是故事的結局。主人翁會得到比原本要探尋的更珍貴的、或是完全不同的什麼。簡單來說,就是領悟。吉爾伽美什沒有找到「不死的祕訣」,相反的,他洞察到了「死亡是無可避免的」。奧德修斯雖然實現了最初的目的,返回了家鄉,但他通過這段漫長的旅程真正收穫到的卻是醒悟。他醒悟到,在這個象徵神的世界裡根本沒有人在意人類的安危;就算是再了不起的英雄也不過是一個人類;人類的一生是建立在脆弱的基礎之上的;幻覺和迷惑帶來的快樂並不是真正的幸福。當奧德修斯回到故鄉達伊薩卡島時,他已經變成了一個跟最初離開時完全不同的人。
電影《溫蒂的幸福劇本》(Please Stand By)的主人翁溫蒂是一個患有自閉症、難以與世界溝通的少女。身為《星際爭霸戰》的頭號粉絲,某天溫蒂看到派拉蒙影業正在公開徵求劇本的消息,她心想如果能拿到獎金就可以從照護機構回家了,於是專心寫起了劇本。但忽然溫蒂捲入了某起事件,無法準時把劇本寄到電影公司。溫蒂決心帶著劇本親自前往洛杉磯,她搭乘巴士有生以來第一次離開了自己生活的地方。溫蒂歷經險阻,不但遇到了沒有禮貌的司機和盜賊,還經歷了車禍。這位符合典型「探尋情節」的主人翁並沒有實現最初的目標──入圍劇本選拔。但她通過這個過程獲得了突破自身侷限的寶貴體驗。雖然溫蒂沒有實現夢想,但觀眾還是為她感到高興。因為在觀看電影的過程中,觀眾醒悟到在溫蒂追求表面目標(入圍劇本選拔)的基礎上,其實存在著真正的內在目標(回歸家庭,走出社會),因此當溫蒂下意識地達成目標時,大家都能發自內心地為她感到高興。
像這樣以「探尋情節」構成的故事大都存在著兩個層次的目標,主人翁表面展現出來的、正在追求的(外在目標)和連自己都不知道的(內在目標)。遵循「探尋情節」創作的故事,會讓主人翁比起追求表面上的目標,更加懇切地去實現內在的目標。這樣的故事才能給觀眾帶來更大的滿足感。
以「探尋情節」分類的故事基本上都在描寫主人翁長途跋涉的旅行。反過來講,遊記都是以「探尋情節」的形式來完成的。我們帶著明確、表面的目標踏上旅途,並且可以把目標隨便告訴周圍的人。比如,到夏威夷學衝浪、到清邁健行、今年暑假去印度練瑜珈,或是走遍歐洲的所有美術館等等。為了實現這樣的目標,我們會做好萬無一失的準備。蒐集當地的信息,預訂住處,研究移動的方法。在「探尋情節」中,主人翁會在終點發現「意外的事實」,然後通過這個「意外的事實」獲得領悟。但在準備旅行的過程中,沒有人會刻意尋找「意外的事實」,製造意想不到的失敗、挫折和出乎意料的結局。每個人都希望旅行一帆風順,平安回家。至少從表面上看是這樣的。但在我們的內心深處,其實存在著連我們自己也沒有意識到的強烈願望。通過旅行發現「意外的事實」,並且對自身、世界有所醒悟,經歷這種魔法般的瞬間,就是我們內心強烈的願望。但這種願望的重點是必須存在「意外」才可能實現,一開始就懷揣這種期待出門是不可能實現的。背後被插了一刀的情況,基本上都是在毫無預料的瞬間發生的。
一直以來,遵循「探尋情節」的小說、電影和遊記受到大眾喜愛的原因,是因為大家都遵循這種情節思考自己的人生。我們的人生也總是存在著外在的目標,考上大學,遇到適合的伴侶結婚、組建家庭,擁有一戶像樣的房子,養育好子女把他們送進大學等等。但不是所有人都能實現這些外在的目標。我們的期待總是高於自己的能力,但即使無法實現預期的目標,也會得到某種程度的滿足,然後不論結果如何都能有所領悟。
美國的某位學者針對職棒小聯盟的選手展開過研究。孩子在開始學打棒球時,都會想「我長大以後,要成為大聯盟的職棒選手。」所有孩子的夢想都是成為大聯盟的職棒選手,而且還是職棒選手中創造輝煌成績的、擁有最高年薪的明星選手。根據thebaseballcube.com從二○○○年到二○○一年的新人選拔結果來看,職業球隊從業餘選手中選拔了一萬七千九百二十五人,但只有一千三百二十六名選手出戰過職業棒球比賽,也就是說還不到百分之七點四。那些只到小聯盟就結束了選手生涯的人都沒有實現最初的目標,但他們並非都是不幸的。雖然這些人沒有獲得巨大的成功,但卻活出了自己的人生。竭盡全力上場比賽,遇到一生摯愛組建家庭,退役後成為教練培養下一代選手,或是乾脆另謀出路。雖然他們在這個過程中沒有實現最初的目標(「成為職棒選手」),但卻收穫了更寶貴(或是自認為更寶貴)的教訓。不管怎樣,大家都堅持過來了。在他們身邊有珍愛的家人陪伴,而且獲得了即使在旁人眼裡看似微不足道,但卻是自己努力一生的小成果。人生和旅行因此充滿了神祕。就算我們無法實現目標,而且還會經歷意想不到的失敗、考驗和挫折,但我們還是可以從中收穫到喜悅和幸福,並且獲得深刻的領悟。
我在自願(?)離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瞬間,在寫作計畫徹底泡湯的瞬間又領悟到了什麼呢?事實上,當時我的腦袋一片空白。臨行前,我對周圍的朋友揚言要去上海寫小說,結果就這麼荒唐無稽地走了一趟。我要如何跟朋友解釋這件事呢?原本計畫要在上海完成的小說,如今該怎麼辦呢?當時,我只在擔心這些事。
我提著行李走出機場,夜已經深了。我不好意思搭計程車,於是走去搭機場巴士。面對早上出國的丈夫遭驅逐出境,夜裡歸家的空前狀況,妻子一時失去了平常心。我勸她說,中國簽證很快就能辦下來,到時候再去也不遲。但妻子阻止我,她說,為什麼還要去趕走你的國家?從明天早上開始哪裡也不要去,就在家裡集中精力寫小說,不要到處宣揚,閉門不出就等於是去了上海。我聽從妻子的話,隔天起足不出戶,埋頭寫起了小說。就這樣,小說趕上了進度。這麼看來,遭遇驅逐出境也不是一件可怕的事,這只不過是先後順序調換了一下罷了。我原本的計畫是出國──上海滯留──寫小說──回國,然後變成了出國──(極短暫的)上海滯留──回國──寫小說。從結果來看,調換順序並沒有造成問題。寒假快要進入尾聲,長篇小說一旦進入寫作狀態,作家就會被帶入另一個世界。正因為這樣,如果作家能真正專注於寫作,自己身在何處也就不那麼重要了。有時,我會乾脆忘記自己身在何處,跟隨著主人翁金基榮,時而走在平壤的街頭,時而走在首爾的樂園商街或韓國世貿中心(COEX)的地下。這讓我幾乎忘記了自己是在上海浦東,還是身在自己家的房間裡。
結束了為期一個月的「自家旅行」後,我在寒冬裡的某一天來到漢江邊散步。我像是剛從海外回來的人一樣,對首爾的一切感到很陌生。記得某位作家前輩在新書上市後接受採訪時說,小說脫稿後走到外面,才發現只有自己穿著冬天的衣服。每天通勤的上班族或許會感到難以置信,但我卻完全明白他講的話。作家比其他職業的人更常去旅行,能為我們的精神世界帶來最大影響的是到自己創造的世界旅行。如果跳進那個兔子洞的話,時間就會變得不一樣,能夠左右主人翁命運的重大事件和矛盾隨即展開,這可要比在現實世界裡旅行更具有戲劇性。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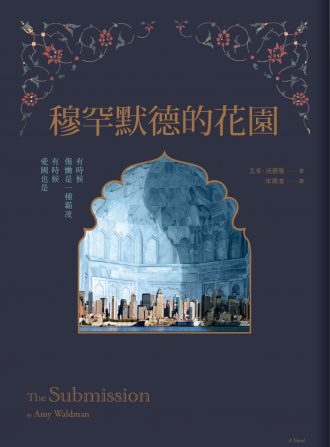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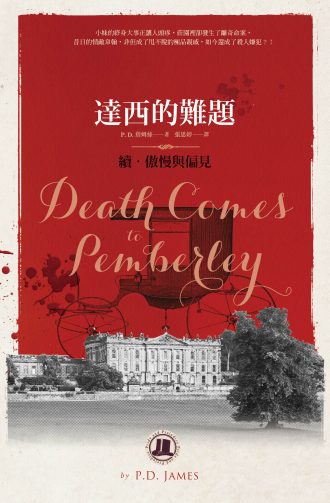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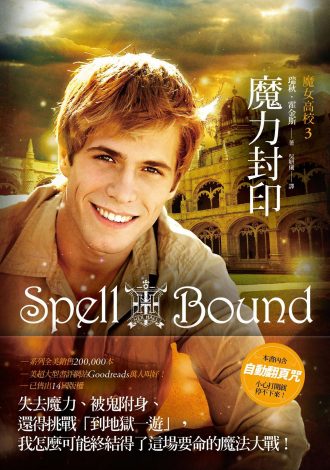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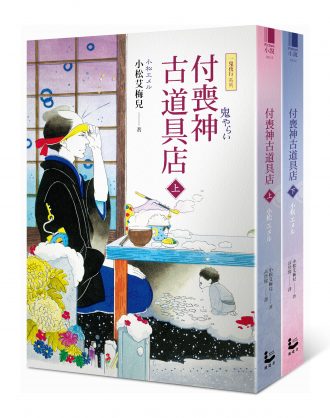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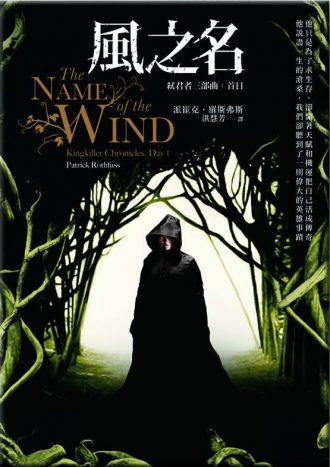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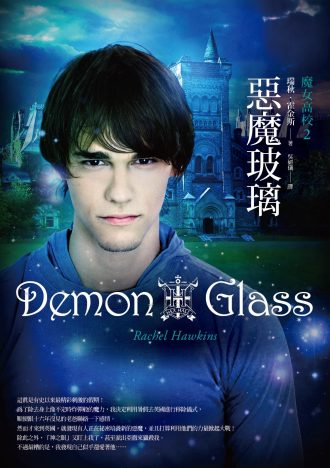

Reviews
There are no reviews y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