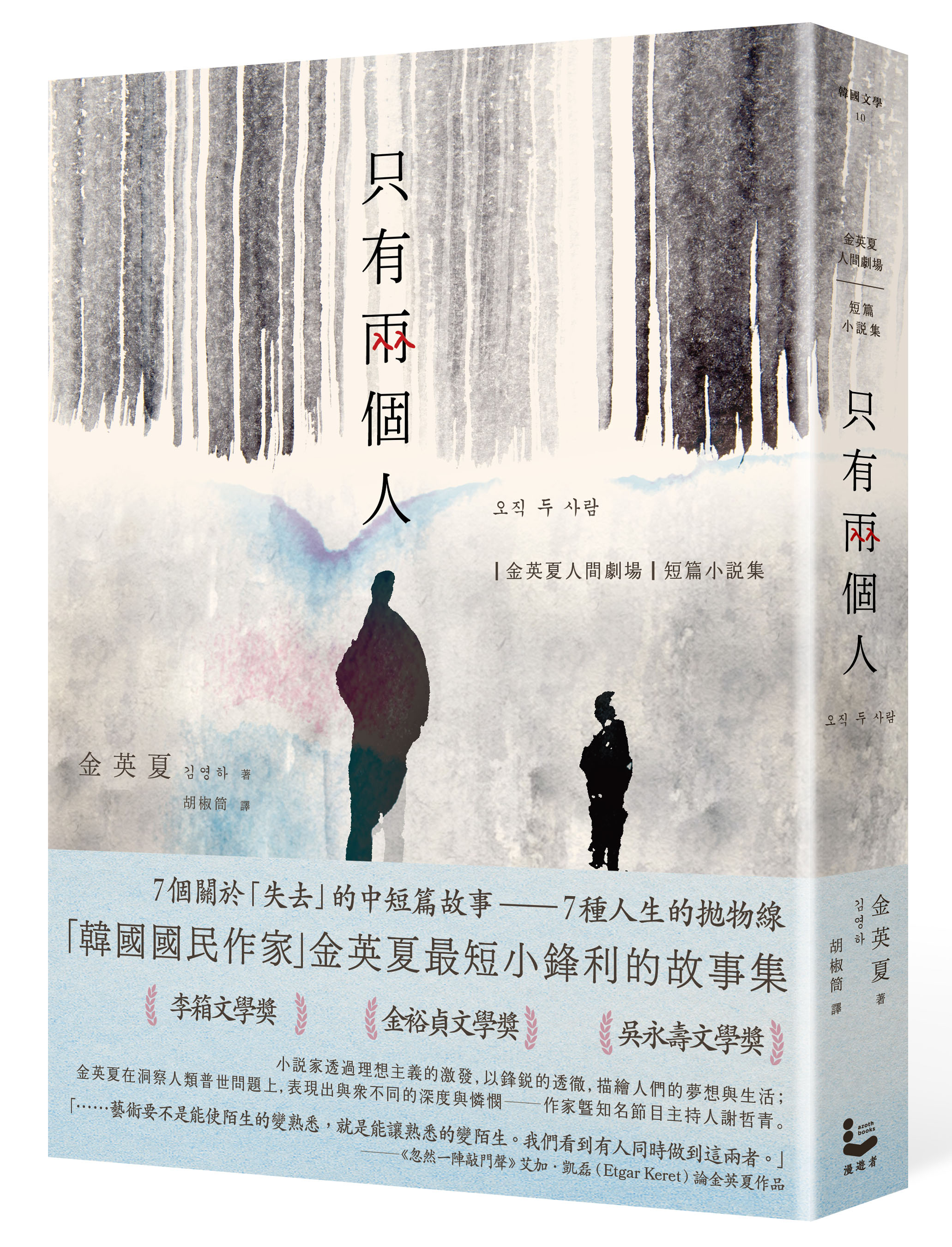仁雅從公寓的陽臺跳樓身亡了。警方公佈的死因是跳樓自殺,但瑞鎮不相信。警方稱:「妻子患有憂鬱症,丈夫出院後,夫妻經常發生爭執。事發當日,夫妻二人又因為看護問題發生爭執,妻子一怒之下衝到陽臺尋了短見。」想到習慣性毆打仁雅的男人,如今竟然不留蛛絲馬跡地殺害了仁雅,瑞鎮就氣憤不已。但僅是情夫的自己又能做什麼呢?如果那時殺了他,仁雅就可那是殺人啊!不是可以輕易做出的決定!不管怎樣,都怪自己當時猶豫不決,所以最終害死了仁雅。瑞鎮的人生原點永遠消失了。瑞鎮不是沒有想過為仁雅復仇,但即使是這樣,仁雅也不可能起死回生。瑞鎮無法忍受看著那個狡猾的加害者逍遙法外,過著悠哉的生活。無論如何,瑞鎮都想毀掉他的人生。
瑞鎮潛伏在仁雅的公寓附近,等待男人現身。他計畫先掌握男人經常出沒的地方和時間點,以便從中找出他的弱點。說不定他會做什麼犯法的事情,比如在公寓裡進行性交易,到時他只需要報警就可以了。但這傢伙可能是因為還在恢復中,所以活動範圍很小:早起到公園散步,然後回家,八點半到位於新城區的投資證券交易所上班,晚上到便利商店採買後直接回家,直到隔天都沒有出門,家裡的燈一直亮到深夜。
瑞鎮發現男人的行動路線過於單純,於是瞄準了清晨的散步路。瑞鎮計畫突然攔下男人,在他沒有設防的情況下,質問他為什麼殺害仁雅。但是當他跟蹤男人走在散步路上時,瑞鎮又突然產生了疑慮:質問他那種問題,讓他不安、內疚,有什麼意義呢?另一方面,瑞鎮也很害怕,他擔心男人會為了煙滅證據而攻擊、威脅自己。正當瑞鎮跟在男人身後、猶豫不決地往前走時,突然有人從水杉林中衝出來,撲倒了男人。
「媽的,你這個殺人兇手,狗娘養的混蛋!」
男人把仁雅的丈夫壓倒在地,然後騎在他身上,一拳接一拳地往他的臉部猛力揮去。仁雅的丈夫面對如同野獸般發出咆哮的男人,絲毫沒有任何防備,讓人感覺他再這麼打下去,真的會鬧出人命。沒多久,仁雅的丈夫被打得滿臉是血。令瑞鎮驚訝的是,毆打仁雅丈夫的男人流下了熱淚,但更令瑞鎮驚訝的是,他在呼喊仁雅的名字。
「仁雅,仁雅啊,都是我的錯,仁雅啊!」
路人蜂擁而至,但所有人都被男人的氣勢嚇呆了,沒有人敢多管閒事。公園管理員剛好經過,這才把男人從仁雅的丈夫身上拉下來。被管理員按住肩膀的男人,衝著躺在地上的仁雅丈夫大喊:他是殺人犯,這個混蛋殺了人。
躊躇地離開現場的瑞鎮來到公司,處理了繁忙的業務,獨自吃了午飯。下午他要去各大醫院推銷產品,其中一間是新城區唯一的大學醫院。瑞鎮經過急診室的時候,突然覺得仁雅的丈夫很有可能被送到這裡。瑞鎮走進急診室,詢問上午是否有腦部受傷的患者被送到這裡。在認識的護士協助下,瑞鎮找到了仁雅的丈夫所在的病床。他閉著眼睛,不知道是在睡覺,還是處在昏迷的狀態。一位上了年紀的老婦人正在看顧他,看樣子應該是他的母親。瑞鎮稱自是人司同事。
「他怎麼樣了?」
「現在腦壓太高了,所以要等腦壓降下來才能做手術。但醫生說,腦壓也有可能降不下來,搞不好會半身不遂,者一輩就這躺在上了⋯⋯」
男人的母親流下眼淚。
「我們家怎麼接連發生這麼不幸的事啊!」
「抓住加害者了嗎?有說為什麼打人嗎?」
老人眼中充斥著怒火,但也許那憤怒的消失點[1]不是針對加害者,而是針對身亡的兒媳,所以她沒有向素未謀面的瑞鎮表露出來。
「沒有,警察說是隨機打人,這世上哪有無緣無故打人的啊?這種人應該拖到光化門的十字路口斬首示眾。」
老婦人了口氣,說道:
「這都是我兒子的命,還能怪誰呢?」
手機響了,老婦人接起電話,走了出去。瑞鎮靜靜地望著男人的臉。那天晚上,仁雅做出了選擇。她在一番深思熟慮後,沒有打電話給那個男人,而是打給了自己。如果仁雅選擇了那個男人,就不會死了,死掉的人一定是眼前的這個人。說不定那個男還會不留跡地處掉屍體,在正和仁雅活在一起。
瑞鎮思考了一下,仁雅死掉和她與那個男人一起生活,哪一種情況更令自己難以忍受。答案似乎是後者更為痛苦。失去了仁雅,他竟然還在想這種事。瑞鎮對自己十分厭惡,但這也由不得他控制。仁雅死了,她的丈夫很快也會死去,或者生不如死,而那個男人會被抓進監獄,眼下只有自己平安無事。想到這裡,莫名的幸福感湧上瑞鎮的心頭。他甚至還覺得很驕傲,因為自己抵擋住巨大的誘惑,而且在危機中守護了自己的安全。人生的原點有什麼用?最重要的是那種精上的奢侈品而是活著本身此時此刻,瑞鎮才有了長大成人的感覺。能告別那個童年閱讀偉人傳記、做白日夢、多愁善感的自己令他感到無比欣慰。
[1] vanishing point,透視法的基本觀念之一,為兩條平行線的最終交會點,落在最遠處的地平線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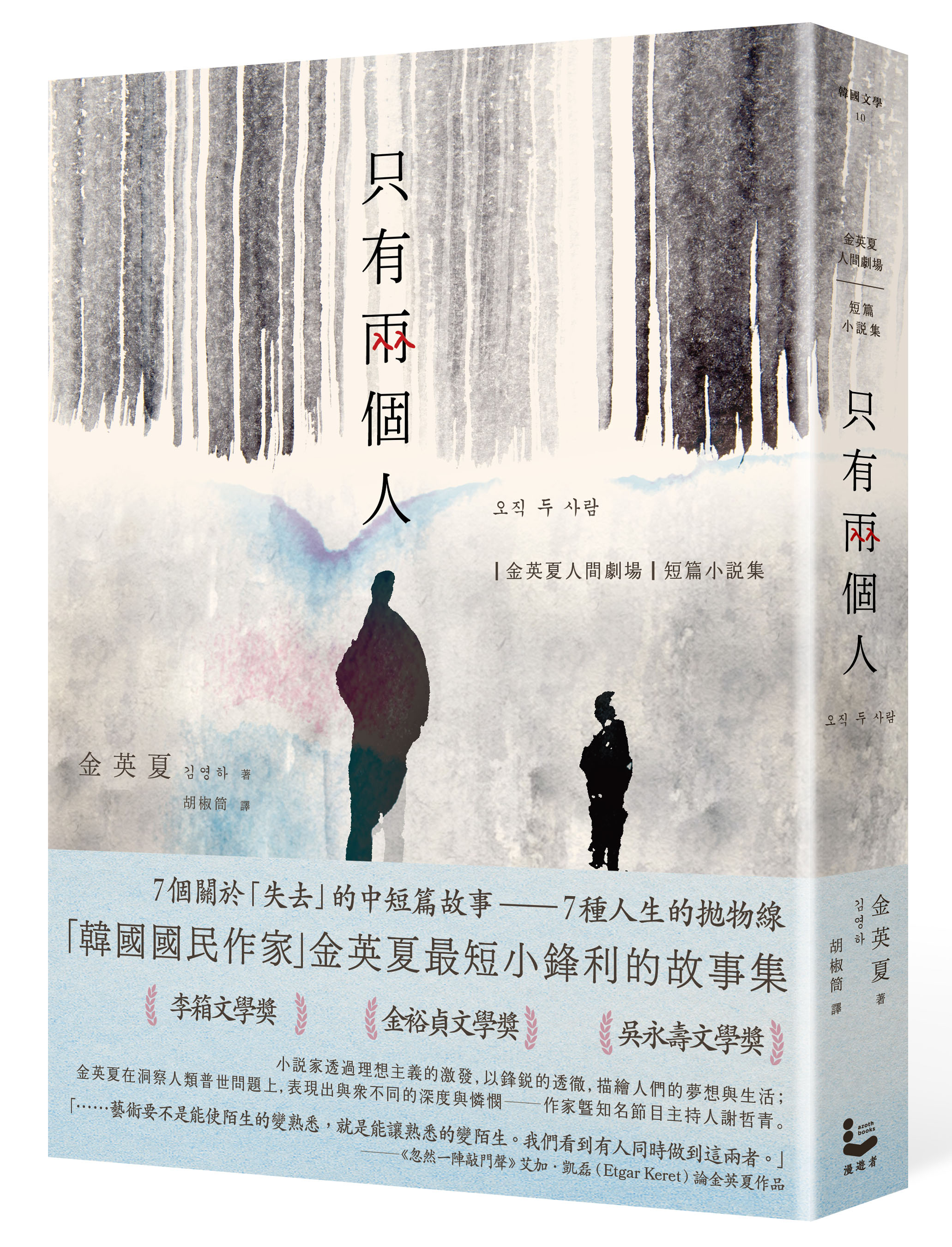
ss”>
仁雅從公寓的陽臺跳樓身亡了。警方公佈的死因是跳樓自殺,但瑞鎮不相信。警方稱:「妻子患有憂鬱症,丈夫出院後,夫妻經常發生爭執。事發當日,夫妻二人又因為看護問題發生爭執,妻子一怒之下衝到陽臺尋了短見。」想到習慣性毆打仁雅的男人,如今竟然不留蛛絲馬跡地殺害了仁雅,瑞鎮就氣憤不已。但僅是情夫的自己又能做什麼呢?如果那時殺了他,雅就不會死。可那是殺人!不是可以輕易出的決定!不管怎樣,都怪自己當時猶豫不決,所以最終害死了仁雅。瑞鎮的人生原點永遠消失了。瑞鎮不是沒有想過為仁雅復仇,但即使是這樣,仁雅也不可能起死回生。瑞鎮無法忍受看著那個狡猾的加害者逍遙法外,過著悠哉的生活。無論如何,瑞鎮都想毀掉他的人生。 瑞鎮潛伏在仁雅的公寓附近,等待男人現身。他畫先掌握男人常出沒的地方時間點,以便從找出他的弱點。說定他會做什麼犯法的事情,比如在公寓裡進行性交易,到時他只需要報警就可以了。但這傢伙可能是因為還在恢復中,所以活動範圍很小:早起到公園散步,然後回家,八點半到位於新城區的投資證券交易所上班,晚上到便利商店採買後直接回家,直到隔天都沒有出門,家裡的燈一直亮到深夜。 瑞鎮發現男人的行動路線過於單純,於是瞄準了清晨散步路。瑞鎮計突然攔下男人,他沒有設防的情況,質問他為什麼殺害雅。但是當他跟蹤男人走在散步路上時,瑞鎮又突然產生了疑慮:質問他那種問題,讓他不安、內疚,有什麼意義呢?另一方面,瑞鎮也很害怕,他擔心男人會為了煙滅證據而攻擊、威脅自己。正當瑞鎮跟在男人身後、猶豫不決地往前走時,突然有人從水杉林中衝出來,撲倒了男人。 「媽的,你這個殺人兇手,狗娘養的混蛋!」 男人把仁雅的丈夫壓倒在地,然後騎在他身上,一拳接一拳地往他的臉部猛力揮去。仁雅的丈夫面對如同野獸般發出咆哮的男人,絲毫沒有任何防備,讓人感覺他再這麼打下去,真的會鬧出人命。沒多久,仁雅的丈夫被打得滿臉是血。令瑞鎮驚訝的是,毆打仁雅丈夫的男人流下了熱淚,但更令瑞鎮驚訝的是,他在呼喊仁雅的名字。 「仁雅,仁雅啊,都是我的錯,仁雅啊!」 路人蜂擁而至,但所有人都被男人的氣勢嚇呆了,沒有人敢多管閒事。公園管理員剛好經過,這才把男人從仁雅的丈夫身上拉下來。被管理員按住肩膀的男人,衝著躺在地上的仁雅丈夫大喊:他是殺人犯,這個混蛋殺了人。 躊躇地離開現場的瑞鎮來到公司,處理了繁忙的業務,獨自吃了午飯。下午他要去各大醫院推銷產品,其中一間是新城區唯一的大學醫院。瑞鎮經過急診室的時候,突然覺得仁雅的丈夫很有可能被送到這裡。瑞鎮走進急診室,詢問上午是否有腦部受傷的患者被送到這裡。在認識的護士協助下,瑞鎮找到了仁雅的丈夫所在的病床。他閉著眼睛,不知道是在睡覺,還是處在昏迷的狀態。一位上了年紀的老婦人正在看顧他,看樣子應是他的母親。瑞鎮稱自己是男人公司同事。 「他怎麼樣了?」 「現在腦壓太高了,所以要等腦壓降下來才能做手術。但醫生說,腦壓也有可能降不下來,不好會半身不遂,或一輩子就這麼躺在床了⋯⋯」 男人的母親流下眼淚。 「我們家怎接連發生這麼不幸的事啊!」 「抓住加害者了嗎?有說為什麼打人嗎?」 老婦人眼中充斥著怒火,但也許那憤怒的消失點[1]不是針對加害者,而是針對身亡的兒媳,所以她沒有向素未謀面的瑞鎮表露出來。 「沒有,警察說是隨機打人,這世上哪有無緣無故打人的啊?這種人應該拖到光化門的十字路口斬首示眾。」 老婦人嘆了口氣,又說道: 「這都是我兒子的命,還能怪誰呢?」 手機響了,老婦人接起電話,走了出去。瑞鎮靜靜地望著男人的臉。那天晚上,仁雅做出了選擇。她在一番深思熟慮後,沒有打電話給那個男人,而是打給了自己。如果仁雅選擇了那個男人,就不會死了,死掉的人一定是眼前的這個人。說不定那個男人還會不留痕跡地處理掉屍體,現在正和仁雅生活在一起。 瑞鎮思考了一下,仁雅死掉和她與那個男人一起生活,哪一種情況更令自己難以忍受。答案似乎是後者更為痛苦。失去了仁雅,他竟然還在想這種事。瑞鎮對自己十分厭惡,但這也由不得他控制。仁雅死了,她的丈夫很快也會死去,或者生不如死,而那個男人會被抓進監獄,眼下只有自己平安無事。想到這裡,莫名的幸福感湧上瑞鎮的心頭。他甚至還覺得很驕傲,因為自己抵擋住巨大的誘惑,而且在危機中守護了自己的安全。人生的原點有什麼用呢?最重要的不是那種精神上的奢侈品,而是活著本身。此時此刻,瑞鎮才有了長大成人的感覺。能告別那個童年閱讀偉人傳記、做白日夢、多愁善感的自己令他感到無比欣慰。 [1] vanishing point,透視法的基本觀念之一,為兩條平行線的最終交會點,落在最遠處的地平線上。